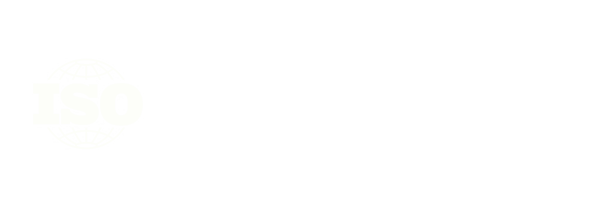《美国争议甘苦谈》 2025上海站讲座摘要实录
2025.05.07 郝勇 徐毓
北京时间 2025年 1月 16 日下午2 点,君合纽约合伙人郝勇律师在君合上海分所举办了关于美国争议解决领域所涉及的主要法律问题的线下讲座,该讲座邀请函请见:1月16日 郝勇《美国争议甘苦谈》2025上海站,具体内容不在此赘述。
本摘要实录所涉内容均为美国公开渠道可获取的信息,不涉及任何保密信息,也不构成任何法律建议。本文仅为基于郝勇律师在讲座现场的发言整理而成的书面文稿,无法准确反映讲座现场的即兴讨论内容。如希望进一步了解相关的案件信息,诚挚建议参与线下讲座的实时互动和讨论。
近期,郝勇律师将于2025年5月15日在北京举行第二期线下讲座,邀请函请见:5月15日 郝勇《美国争议甘苦谈》2025北京站,诚邀各位参加。
本文由君合纽约办公室律师徐毓协助准备,由实习生向雨辰和王浩川根据线上讲座内容整理,特此感谢。此外,特别鸣谢君合上海分所合伙人王钊律师为上海站讲座开场致辞。
1. Am. Girl v. Zembrka (2024 U.S.App. LEXIS 23555)
这个案例是近年来美国知识产权与电子商务管辖权领域的一个重要案例。本案原告American Girl 是在美国做洋娃娃非常有名的公司。被告Zembrka在亚马逊上有个网店,仿造American Girl的产品,其仿造品和正品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当境外电商通过互联网向美国消费者销售侵权商品时,如果交易未最终完成,美国法院是否仍可对其行使管辖权。
对于在美国法院被诉的中国客户来讲,管辖权是要关注的第一个问题,因为这是一个门槛性(threshold)的问题:如果能证明法院没有管辖权的话,中国客户就无需参与后续诉讼程序。很多中国客户在美国打官司时是被告,但没有这个概念,以为管辖权没有争议,但真实情况不是这样的。我们在处理几乎每件案子时,第一件事就会提出管辖权异议,且可能双方争议到最后的就是这一个问题。
在美国,管辖权简单来讲分为属人管辖权(personal jurisdiction)和事项管辖权(subject matter jurisdiction),而属人管辖权又分为一般属人管辖权(general personal jurisdiction,简称general jurisdiction)和特别属人管辖权(specific personal jurisdiction,简称specific jurisdiction)。
中国公司一般争议的主要是特别属人管辖权,其有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最低联系”(minimum contacts),即当中国公司有意地与美国某一司法辖区产生最低限度的联系时,美国法院就可以对其行使管辖权。例如,如果中国公司与当地消费者或店家主动建立联系,并针对当地消费者积极开展业务,法院可能会认定该公司有意地利用(purposeful availment)了在该辖区开展业务的好处。
第二个要素是“关联性”(relatedness),即诉讼事项是由该公司的“有意利用”所引发的。例如,一名律师主动在纽约州拉客户,又在纽约州被起诉证券欺诈,但证券欺诈不是该律师到纽约拉客户引发的,所以法院可能缺乏管辖权。
第三,行使管辖权必须符合美国宪法的“正当程序原则”(due process)。
在本案中,问题的关键在于判断被告是否构成“有意利用”美国市场,以及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与被告在美国的商业活动存在充分联系。传统上,美国法院对境外被告的管辖权认定较为谨慎,通常要求被告与管辖地存在实质性商业联系,例如实际完成交易、投放定向广告或设立实体经营场所。然而,随着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法院开始重新审视这一标准,特别是在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
本案有一个关键点是被告有一个互动性的网站,因为有互动性的网站说明被告非常踊跃地去建立“有意利用”。如果网站不是互动性的,那被告可以说它不是主动地去接触相关消费者;如果网站是互动性的,即消费者可以提供自己的信息、下单、付款,则法院通常比较容易建立特别属人管辖权。在本案中,有纽约的消费者购买了被告的产品,但在下单之后,被告可能发觉会有人来告它,于是把订单取消了,导致交易本身并没有发生。
本案的一审法院(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采纳了相对保守的立场,认为由于被告最终取消了订单,交易并未实际完成,因此被告并未真正“利用”美国市场,所以法院缺乏管辖权。然而,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在二审中推翻了这一裁定,并提出了更具扩张性的管辖权认定标准。第二巡回法院首先强调,被告运营的是一个高度互动性的商业网站,消费者可以浏览商品、提交订单并进行支付。这种商业模式本身就表明被告主动接触美国市场开展业务,属于“有意利用”。同时,原告起诉的是知识产权侵权,至于交易是不是实际上发生了、货有没有运到、或款项有没有支付并不重要。因此,第二巡回法院作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裁定。
这个案子对于中国企业,尤其是电商及其他在网上开展美国业务的公司来说,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案子。美国的很多案例,尤其在第二巡回法院的案例,大多时候对管辖权采取的是非常严格的判定。然而,这个案件的判决实际上可以说是降低了标准,使法院更容易建立管辖权。
2. Hawkeye Gold v. China Nat’l Materials Indus. Imp. & Exp. (2023 U.S.App. LEXIS 33531)
这个案例是在第八巡回上诉法院审理的。原告Hawkeye Gold是密苏里州一个卖农产品的公司,卖了一批转基因的农产品给中材国际(China National Materials Industry,“母公司”)在美国的子公司Sinoma(“子公司”)。交易发生后,在大约十年前,当货物还没有进入中国港口时,中国出台了一些转基因的禁止措施,导致货物没有办法进入港口。
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当外国母公司参与子公司在美国的商业活动时,美国法院能否基于“刺穿公司面纱” (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理论对母公司行使特别属人管辖权(specific personal jurisdiction,简称specific jurisdiction)。
在美国,法院可以基于特别属人管辖权的理论对中国实体行使管辖权,而这也是中国公司一般在美国应诉时的主要争议点。如果要建立特别属人管辖权,原告需证明三个要素,即中国公司通过“有意利用”(purposeful availment)美国某一司法辖区与该辖区产生了“最低限度的联系”(minimum contacts),诉讼事项与该公司的“有意利用”存在“关联性”(relatedness),及法院行使管辖权符合美国宪法的“正当程序原则”(due process)。
本案关于管辖权的争议集中在第一个要素,即涉案的中国公司与美国的联系是否达到了“有意利用”的标准。然而,使本案更为复杂的是其中涉及到子公司和母公司之间的关系。如果中国母公司很大程度上控制和主导了美国子公司的事务,以至于美国子公司的存在可以被忽视,则法院可能会“刺穿公司面纱”,基于其对美国子公司的管辖权从而对中国母公司行使属人管辖权。
本案原告起诉子公司合同违约,并在一审中胜诉,但子公司随后破产,无力支付赔偿。这是一个关键情况,因为原告起初并没有起诉母公司。由于拿不到赔偿,原告在2016年又通过“刺穿公司面纱”理论起诉了母公司,要求母公司承担子公司的法律责任。原告给出了很多理由,比如当时在跟子公司签订销售合同的时候,母公司派人一起来进行谈判,而子公司买了案涉货物后又转手卖给母公司。这都是常见的针对中国公司的“刺穿公司面纱”的论点,因为其在美国的子公司多半已破产。
在过去十年里,一审法院和上诉法院都认为母公司与美国的联系不足以建立特别属人管辖权。首先,母公司本身没有专门接触美国。尽管它派人去谈判,但它没有达到“有意利用”的标准。这个问题很复杂,涉及很多主观因素,比如在什么情况下造成了足够多的联系,以及假设母公司派了一个代表去,又在什么时候造成了有目的的接触。
本案最终判定母公司本身的接触没有达到标准,且母公司和子公司间的关系比较清楚,达不到“刺穿公司面纱”的标准,但在这个过程中,第一个官司打了十年,最终在上诉法院获得了最终判决。
基于本案的经验教训,跨国经营企业应当特别注意以下几个合规建设:在交易结构设计方面,应当明确子公司的独立法律地位,保留完整的董事会决议记录等公司文件;避免母公司人员直接参与合同签署等具体经营行为;建立有效的防火墙制度,包括使用独立的企业邮箱系统等隔离措施;在争议解决条款的设计上,建议考虑约定仲裁条款来排除法院管辖。
3. In re TikTok (2023 U.S.App. LEXIS 28880)
本案是北京美摄公司对TikTok提起的知识产权诉讼,核心争议聚焦于审理地移送问题。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的裁决不仅对本案产生直接影响,更为跨国企业在美诉讼策略提供了重要参考。
美国共有九十四个联邦地区法院,其中每个州至少有一个联邦地区法院,而一些大州(如纽约、德州、加州)则有多个法院。审理地问题关乎由九十四个法院中的哪个法院来审理某一特定案件。被告可以提出将案件从一个地区法院移送(transfer)到另一个地区法院,但需要提供充分的理由,例如:主要证人、文件、证据在哪个地区更为集中;争议事件发生在哪里;案件与哪个地区的联系更为密切等。
本案中,TikTok作为被告在德州西区法院被北京美摄公司起诉。被起诉后,TikTok立即提出将案件移送至加州北区法院的动议,这一请求基于几个关键事实:首先,TikTok的美国业务总部位于加州,绝大多数高管和核心技术人员都在该地区工作;其次,与案件相关的主要证据和文档资料也集中存储在加州;最后,加州北区法院在处理类似科技公司知识产权案件方面具有更丰富的经验。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TikTok主张移送审理地的实质性理由。
对此,美摄公司提出了强有力的反对意见。该公司提出,TikTok在德州同样设有办公室和工作人员,这些人员对案件涉及的技术问题具有充分的了解,完全可以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根据“一百英里规则”(100-mile rule),证人需要旅行一百英里以内以参与诉讼完全在合理通勤范围内。更重要的是,案件在德州西区法院已经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诉讼程序,双方都投入了大量时间和资源。如果此时变更审理地,不仅会造成诉讼程序的重复和浪费,还需要新的承办法官重新熟悉案情,这显然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
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的裁决体现了对司法效率的高度重视。法院在审查此案时发现,一审法院在审理移送动议时存在严重拖延,从TikTok提出动议到法院作出裁定竟然耗费了一年多时间。这种拖延不仅违反了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对及时裁判的要求,更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造成了实质性损害。上诉法院特别批评了一审法院的裁判逻辑,指出其以"诉讼已进行一年"为由拒绝移送,却忽视了正是法院自身的拖延导致了这一状况,这种循环论证的做法明显违背了司法公正原则。
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的法律概念,叫“writ of mandamus”(执行职务令),即上诉法院对于一审法院提出严厉批评,发出命令,强制要求一审法院把案件转走。法院最后下令将案件移送到加州北区。
值得注意的是,管辖权与审理地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审理地移送阶段,管辖权问题可能还没有确定。换言之,一个案子已经打了一年,但管辖权仍可能未被确认,审理地A或B都可能有管辖权。当事人提出移送审理地的动议,可能并非基于管辖权,而是出于对某地区、法官的偏好,或认为某地陪审团更有利。
4. Riot Games v. Shanghai Moonton Tech. (2022 U.S. Dist. LEXIS 216832)
本案涉及一起复杂的跨国知识产权纠纷,牵涉三家游戏公司的法律角力。上海沐瞳科技有限公司(Moonton)作为被告,同时面临来自美国拳头游戏公司(Riot Games)及其母公司腾讯的两线诉讼。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在于跨国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管辖权冲突与证据获取障碍引发的程序正义问题。
如果某一诉讼在其他国家的法院进行更为便利时,美国法院可以基于辖区不便(forum non conveniens[JH1] )原则驳回诉讼。辖区不便主要考虑的是“国际礼让”(international comity)。即使美国法院有管辖权审理案件,但如果另一个国家也有管辖权且审理更为便利,出于国际礼让,美国法院也可以将案件审理让出去。
本案中,被告Moonton在美国被Riot Games起诉知识产权侵权。Riot Games的100%控股母公司是腾讯,而腾讯也在中国起诉了Moonton。Moonton是中国公司,在中国和美国都有运营地,这也是为什么其可以同时在美国和中国被起诉。Riot Games是美国公司,在美国和中国都有运营地,而美国法院对腾讯没有管辖权。这种双重诉讼策略引发了Moonton的核心抗辩:如果其侵犯的是Riot Games的权利,那么腾讯应该退出;如果两家公司都主张对同一游戏内容享有知识产权,那么要么其中一方的主张不成立,要么说明该游戏内容本身缺乏足够的原创性。
案件的关键难点在于证据获取。法院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腾讯是至关重要的第三方,需要腾讯来证明自己是怎么开发这些游戏的,包括跟Riot Games之间有没有许可(license)。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美国法院对腾讯没有属人管辖权,因此没有办法通过发传票(subpoena)等证据开示(discovery)方式迫使腾讯交出这些信息。但是,如果Riot Games在中国起诉Moonton,也许中国法院可以要求腾讯向中国法院提交证据。根据美国法典第28章第1782条,外国诉讼方可以向美国法院提出申请,要求美国法院强制让美国的一个案外人提供证据。这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法条,因为全世界任何地方的取证程序都没有美国的取证程序这么有侵略性和耗费时间、精力和金钱。
然而,本案的不对称性在于,涉案方在中国可以要求在美国取证,但反过来不行。因此,Moonton没有办法通过中国法院获得信息。这是这个案子的关键。加州中区法院基于这点考虑决定,即使其对当事方有管辖权,但仍然存在辖区不便的问题。法院强调,腾讯是个关键的存在。如果不存在腾讯和Riot Games的这层关系,那就没有这个问题。Riot Games和腾讯想要在战略上两面夹击,同时法院邀请腾讯自愿加入本案,以便法院继续审理。这里还有一个细节是,腾讯表示其愿意签订协议,提供在中国法院做的证据开示给美国法院使用,但美国法官并不认可,因为证据开示不是涉案方想开示什么就开示什么。如果涉案方同意在美国接受法院管辖权,那么其就需要根据其他方的请求开示相关证据。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本案的启示在于:在规划全球知识产权战略时,必须充分考虑不同司法管辖区的程序差异;面对平行诉讼时,要善于利用程序规则来维护自身权益;同时,也要注意母子公司之间的法律界限,避免因关联关系导致不必要的诉讼风险。随着数字经济的全球化发展,这类涉及多法域的知识产权纠纷可能会越来越多,企业也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法律风险防控机制。
5. Frisch v. Shanghai Huayi Grp. (2023 U.S. Dist. LEXIS 85336)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跨国产品责任纠纷,涉及复杂的管辖权争议和程序规则适用问题。在本案中,美国人Frisch起诉上海华谊(轮胎制造商,曾叫“双钱轮胎”),起因是一辆垃圾车的轮胎爆裂导致车辆失控,撞到了原告的车,导致原告受了重伤。上海华谊作为制造商被原告起诉,其他被告还包括供应商、经销商、汽修公司、垃圾车司机等。
美国有两套并行的法院系统,州法院和联邦法院。五十个州有五十套自己的法律系统,且各州之间很可能存在差异。州法院和联邦法院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简单来讲,州法院系统只要有属人管辖权,就可以管任何事项,但联邦法院事项管辖权有限,只有特定的事项才能到联邦法院去。
联邦法院的事项管辖权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联邦问题管辖权(federal question jurisdiction),比如专利和商标问题。第二类叫“异籍管辖权”(diversity jurisdiction),即原告和被告异籍,来自不同的州或国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涉案一方在特拉华州,另一方在纽约州,双方现在打官司就有可能在联邦法院进行,因为案件涉及到两个州。然而,如果双方都在纽约州,则不可以在联邦法院起诉。同时,双方也可以在州法院进行诉讼,因为有些法院有“共同管辖权”(concurrent jurisdiction),即联邦和州法院同时都有管辖权,而这就涉及到“移送”(removal)的问题。
异籍管辖权要求“完全异籍”(complete diversity)。比如,如果“v.”的两边(原告v. 被告)各有三方,那么两边不能有重合,其中左右各有一个在特拉华州都不行,需要左右完全不一样才满足要求。完全异籍在合伙制企业(partnerships)的情况下怎么判定很复杂,因为合伙制企业是可穿透的,判定它的州籍或者国籍要穿透到合伙人个人的州籍或国籍。
本案从一开始就呈现出特殊的法律特征:原告是爱荷华州居民,而被告中既有爱荷华州本地企业,也有中国公司上海华谊。这种混合被告的组合意味着案件最初并不具备联邦法院审理所需的“完全异籍”要件。案件的核心争议焦点在于:在原告主动撤销对爱荷华州本地被告的起诉后,上海华谊能否成功将案件从州法院移送到联邦法院。
从案件发展过程来看,原告Frisch在诉讼进行一年之后,发现爱荷华州的被告严格意义上没有责任,并主动撤销对爱荷华州被告的起诉。因此,上海公司发现原被告之间有了完全异籍,便申请将案件从州法院移送到联邦法院。要申请移送的原因可能涉及多种因素,例如部分观点会说,对于较复杂的涉外案件,联邦法院可能更有经验。
从州法院移送到联邦法院在涉及中国当事方的案件中并不少见。根据美国法典第28条第1446编(28 USC § 1446(a)),移送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在案件开始后一年内提出移送申请。在本案中,上海公司就错过了这个期限。然而,移送还有一个例外情况,即法官认定原告当初在州法院起诉是出于“恶意”(bad faith)。比如,原告为了破坏完全异籍,故意把爱荷华州的两个被告加进去,再故意在第一年零一天撤销起诉,这个就属于“恶意”。因此,本案的核心就是原告加入爱荷华州的被告是否是出于“恶意”。法官认定没有恶意,因为原告是在专家评估报告结果出来后才决定撤销起诉。这个因素的判定是非常基于具体事实的。在有些案件中,原告在起诉一年零三个月后就对被告撤销起诉,而法院认定存在恶意;在部分其他案件中,原告在起诉一年零八个月后撤掉被告,而法官认为不存在恶意。
值得注意的是,移送失败并不意味着案子就输掉了。案件可以继续在州法院进行,上海华谊仍然可以在实体层面进行抗辩,包括对产品缺陷的认定、因果关系证明以及损害赔偿计算等问题进行争辩。然而,管辖权层面的失利可能对后续诉讼策略产生影响,包括证据开示的范围、陪审团的组成以及可能适用的州法律等。
6. Netlist v. Montage Tech. (2023 U.S. Dist. LEXIS 68527)
本案起源于Netlist公司对三星电子提起的专利侵权诉讼,核心争议焦点在于:美国法院能否基于对境内子公司的管辖权,强制要求境外母公司提供与诉讼相关的证据?这一争议直接触及跨国知识产权诉讼中证据开示的边界问题。
美国诉讼中大部分的时间、精力和成本都是花在取证(discovery)上。在取证过程中,律师一般可以自己发送传票(subpoena)。例如,我们在有些案件中需要查被告的资产所在地,而由于美国很多公司的资产都是经过一个中转地,比如用人民币支付墨西哥比索需要通过纽约的摩根大通,我们就可以向摩根大通发送传票。摩根大通虽然是世界最大的银行之一,但其如果不回应传票则会构成藐视法庭。美国很多公司有专门负责回复传票的法务。
在本案的取证过程中,原告Netlist向案外人两个Montage公司,即Montage上海及其加州的子公司,发送传票,要求其提供跟起诉三星有关的信息,以证明三星专利侵权。Montage上海抗辩的理由为,其加州子公司根本没有参与Montage和三星的业务来往。虽然Montage和三星有业务来往并因此才会收到传票,但是它们的业务来往都是通过上海母公司进行的。事实上,Montage公司内部(上海母公司和加州子公司)设有严格的防火墙,信息都是不互通的。加州子公司主要负责面向终端客户的市场推广,不涉及核心技术,更没有参与上海母公司和三星的业务来往。因此,尽管Montage加州子公司在法院的管辖区内,但加州子公司没有参与母公司的业务往来,加州地区法院也在本案中对子公司没有管辖权。
这个案件凸显了美国诉讼程序中两个关键法律原则的碰撞。首先是正当程序原则(due process)。作为美国宪法第五和第十四修正案的核心内容,正当程序原则要求任何司法行为都必须遵循基本的公平正义标准。尽管传票效力很强,但其也要受制于正当程序,因为在美国,宪法的效力最强,而宪法的核心就是两个字:due process。加州地区法院认定,尽管Montage加州子公司在法院管辖范围内,但由于其并未实际参与母公司与三星的业务往来,强制其提供证据将违反正当程序原则。法院特别强调,传票的强制力必须受到宪法原则的限制,不能仅因子公司位于管辖区内就推定对母公司也拥有管辖权。
其次是关于传票要求开示的证据具体认定标准。本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按理说管辖权都是针对被告而做的判断,但本案中Montage母公司和子公司均不是被告,而是案外人。因此这个案件也说明,美国联邦法院系统关于能否强制案外人开示证据及是否有具体的判定标准等问题并没有明确的说法。法院在案卷的第七个脚注里说,第二巡回法院看起来是唯一一个考虑过这个问题的,并认为可以援引属人管辖权的标准。
具体来讲,“有意利用”在这个案件里是指,虽然子公司和母公司之间有一定的联系(比如母公司通过子公司开展市场营销和展会等),但有没有联系本身不是问题关键。关键在于,Netlist传票所要求Montage上海子公司提供的信息具体是什么,以及信息是否与子公司和母公司之间的联系有关。如果有关,那么法院可以建立一个特别管辖权。然而,本案法院认为Netlist和三星的纠纷所涉及信息和该联系无关,因此法院并没有强制要求Montage回应传票的权限。进一步延伸,如果能够证明属人管辖权的因果关系,那就意味着美国法院对境外的被送达传票的公司依然拥有特别的属人管辖权(长臂管辖,long-arm jurisdiction),但美国的十三个巡回法院对此尚未达成一致意见。
值得关注的是,本案裁决可能产生的长远影响。如果未来有法院采取更为扩张的立场,认定对境内子公司的管辖权可以延伸至境外母公司,那么可能会确立一种新型的证据开示“长臂管辖权”。这种趋势可能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包括促使跨国企业重组其全球架构以规避风险等。目前已有迹象表明,某些巡回法院可能倾向于扩大解释管辖权范围,而这预示着未来类似案件中可能出现更激进的证据开示命令。
7. Whaleco v. Shein Tech. (2024 U.S. Dist. LEXIS 14894)
本案涉及两个快消巨头公司。原告Whaleco是现在在美国如火如荼的Temu的母公司,而被告是Shein。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在于:在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法院应如何在确保审判公开透明的同时,保护第三方商家(如供应商)的隐私权益。
美国法院通常要求所有的诉讼案件卷宗全部公开,从起诉状、送达证明、庭审卷宗,到向法院提交的送达文件,但当事方在特定的条件下(如涉及未成年人、隐私或敏感信息)可以要求遮蔽相关信息。在决定是否需要遮蔽本应公开的卷宗信息时,法院通常需考虑多个因素,包括公众对相关文件的访问需求、相关文件已被公开的程度、是否已有人反对公开文件及反对方的身份、反对公开文件一方所提出的财产和隐私利益的重要性、公开文件可能对反对方造成的偏见、及在司法程序中引入相关文件的目的等。法院只有在整体考虑过相关因素并认为基于相关因素的考量强烈反对公开相关文件的情况下,才会允许遮蔽相关信息。
本案中,Temu指控Shein的网站使用了很多Temu商家的照片,从而侵犯了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DMCA)。为证明侵权,Temu提交了部分商家的宣誓书(affidavit),其中一些商家实名作证,另一些则匿名。Temu申请遮蔽部分商家信息,但华盛顿特区法院最后认定要公开包括宣誓书在内的所有的信息,以确保司法程序的透明度。
这一裁决引发了关于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与个人隐私保护的激烈辩论。Temu还提出,能否将相关信息只提供给Shein的律师看而不放到法院的网站上,且要求Shein不可以将信息披露给它的客户。对此,法官予以否认,因为Shein需要知道具体信息,包括第三方的名称,来做出有效的抗辩。Temu声称公开第三方信息会使其被迫害,但Temu并未提供被迫害的证据。
总体来讲,本案裁决可能对电商行业及知识产权诉讼产生深远影响。首先,法院的立场虽然维护了司法透明,但也可能造成“寒蝉效应”(Chilling Effect),使更多商家不愿参与诉讼。如果供应商担心实名作证会导致商业关系破裂、竞争对手打压、或网络骚扰,他们可能选择保持沉默,而非协助平台维权。这种“寒蝉效应”可能削弱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尤其是在依赖第三方证言的电商侵权案件中。
其次,本案揭示了电商平台在维权时的两难处境:若要求商家作证,则商家需承担信息公开的风险;若不提供足够证据,则难以证明侵权。未来,平台可能需要在用户协议中提前明确商家信息的披露义务,或探索替代性证据(如匿名聚合数据)来降低隐私担忧。再次,不同司法管辖区之间可能存在潜在分歧,其他法院或许会对遮蔽申请更宽容。这种分歧可能导致原告选择对己方更有利的管辖法院。
对于中国跨境电商而言,在发起或应对知识产权诉讼时,企业应评估证据公开的后果。例如,Temu可尝试通过技术手段证明侵权,而非仅依赖商家证言;Shein则可主张原告未充分保护第三方隐私,以质疑证据的可信度。同时,企业应该关注司法趋势与立法动态,例如美国国会可能针对此类案件修订DMCA或《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并增设电商知识产权诉讼的特殊遮蔽标准。
8. Williams v. Binance (2024 U.S.App. LEXIS 5616)
这个案件是比较前沿的证券诉讼案件。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在于:对于宣称“去中心化运营”的加密货币交易所,美国法院能否依据其实际商业联系行使证券法管辖权。
当一个案件涉及使用美国法律去管辖外国主体时,美国法院长期保持了一个原则,即美国国会的立法旨在仅在美国的领土管辖范围内适用,除非所涉法案中有相反的意图。因此,当一项法律未明确表示其具有域外适用性(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时,该法律就不应在美国的领土管辖范围外适用。
在涉及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the Exchange Act of 1934)的案件中,美国最高法院在考虑到国际礼让原则及需避免与其他国家适用法律不兼容的情况后认为,《1934年证券交易法》仅适用于在美国国内交易所上市的证券及其他证券在美国国内的交易。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在涉及美国各州证券法的案件中也适用了相同的原则。
本案被告币安是在中国成立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原告Williams是其投资人之一,买了加密货币,但遭受了损失。这个案子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被告声称法院对其没有管辖权,因为币安是“去中心化”运营的。法院引用了很多次币安创始人赵长鹏2020年2月针对马耳他监管机构否认币安是一家“总部位于马耳他的加密货币公司”时所提出的说法:
“Binance.com 的总部或运营地并不在马耳他……有些人对世界应该如何运作存在误解……他们认为必须要有办公室、总部等等,但现在我们处于一个区块链的新世界……Binance.com 一直以去中心化的方式运营,我们与全球180多个国家的用户保持联系。”
这里需额外说明,赵长鹏的最后一句话“与全球180多个国家的用户保持联系”(“reach out to... more than 180 nations worldwide”)很危险,可能会被法院视为等同于自己承认了法院对其有管辖权。在本案中,第二巡回法院认为其对币安有管辖权,因为币安在美国境内使用的是亚马逊的云服务器。虽然法院不能百分之百确定原告做的所有交易都是在这个服务器上运行的,但因为原告基本都是美国个人或公司,交易也基本都是以美元结算的,法院认为在案件的初级阶段,可以默认币安使用了美国的服务器。因此,法院对其有管辖权。
法院同时提出,币安“臭名昭著地”(notoriously)否认了全世界任何地方的证券交易规则,因此法院必须要以正视听。既然币安提出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对其有管辖权,那么美国法院用美国的证券法对其行使管辖权就不会有国际礼让原则的顾虑了。因此,赵长鹏这段发言不仅承认了美国法院对币安有管辖权,甚至还邀请了美国法院对其进行管辖。
另外,该案件还涉及到诉讼时效的问题。证券诉讼的时效一般较短,只有一年。很多投资人跟币安签署了使用条款(Terms of Use),但在签署之后的很长时间内都没有下单。但当投资人等到下单并受到损失后再起诉时,距离签署使用条款已经过去了一年。这里的问题在于诉讼时效从什么时候开始起算。币安声称应该从签署使用条款开始起算。法官指出,这样会造成很多不公正的结果,因为如果等到一年之后再下单,那任何交易都过了诉讼时效。因此,诉讼时效应该从下单之日起开始计算。
9. Bai v. N.Y.C. Reg’l Ctr. (2023 U.S. Dist. LEXIS 174158)
这个案件涉及纽约市华盛顿桥(George Washington Bridge,连接曼哈顿和新泽西)纽约端的巴士站重建项目。该项目花了上亿美元,并通过EB-5区域中心吸引了大量中国投资人。项目破产后,很多投资人起诉,要求赔偿5778万美元。原告的主张首先是他们受到了欺诈,因为他们在签署有限合伙协议(包括招股说明书和认股协议)时只收到了签字页,并未看到完整的文件。虽然项目的普通合伙人(General Partner,GP)口头承诺了某些抵押物,但原告后来发现这些承诺是虚假的,可口头承诺缺乏书面证据。第二,即使他们收到了任何文件,他们也看不懂,因为文件均是英文文件。
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在于:在跨国投资合同中,当投资者主张因语言障碍或文件不完整而遭受欺诈时,法院应如何在维护合同严肃性与保护弱势投资者权益之间取得平衡。
在EB-5投资移民中,多数情况下中国投资人都是作为有限合伙人(Limited Partner,LP)通过区域中心参与,投资一个有限合伙企业(Limited Partnership),由发起人做普通合伙人,有限合伙企业作为贷款人再把这些有限合伙人汇集起来的钱作为贷款借给项目中心。在这里,投资人是次级贷款人(subordinate lender),权益相对有限。具体来说,假设一个项目需要一亿美元资金,其中三千万来自股权,七千万来自债务,而摩根大通作为优先债权人提供了五千万贷款,有限合伙企业作为夹层贷款人提供了两千万贷款,这两千万由四十名中国投资人每人出资五十万美元组成。
作为投资人,即使每个人都有抵押物,但由于其是次级贷款人,抵押物价值也大打折扣。在这个例子中,项目出事后可能只值六千万,而摩根大通作为优先债权人可以收回五千五百万(包括利息),那么中国投资人的两千万实际上最后只能收回五百万,股权则可能就全部没有了。
作为有限合伙人,投资人的权利非常有限。根据《有限合伙协议》和《招股说明书》,所有事情都是普通合伙人来做,而普通合伙人在其中能挣很多钱,相当于拿手续费加提成,从每个五十万中挣出三十万,其中就可能有很多欺诈行为。对于中国投资人来讲,他们可能意识不到自己实际支付了八十万,因为其中很多是利息,而利息被普通合伙人吃了。之所以利息高,是因为他们是次级贷款人,有较高的风险。
在本案中,纽约法院在判决中指出,根据纽约法律,除非存在胁迫等特殊情况,只要签署合同,则签署方即被视为已经阅读并理解了合同内容。法院认为,投资人不能以“未阅读”或“不懂英文”为由主张欺诈或合同无效,因为既然签署方已经同意了合同,那么就不存在欺诈行为。法院进一步指出,对于不懂英文的情况,投资人可以在签署前寻求法律或翻译帮助,以确保他们理解合同条款。因此,法院驳回了原告的欺诈指控,认为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
对于这点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从投资人的角度出发,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些投资人是消费者,是弱者,而从保护消费者的立场出发,也许可以有不同的结果。以上述提到的使用条款为例。假如用户在网上点击签字,但如果一点击就把自家房子卖了,而用户说没看清条款内容,那么应该如何判定?什么事可以,什么事不可以,又应该如何做界定?
另一方面,从法律角度来看,法院判决强调了合同的严肃性和可预测性。法院认为,合同(尤其是商业合同)的有效性不应该因一方的事后反悔而受到质疑,不然有很多原告都可以提出类似的诉讼,很难理清。法院在本案中更倾向于维护合同的严肃性和终局性以及商业交易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