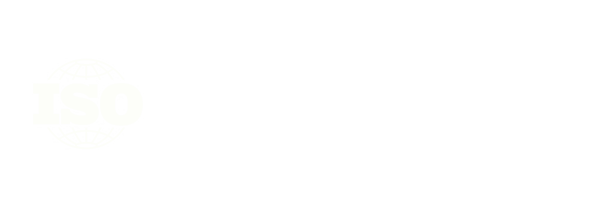数字时代下体育赛事转播权的维权困境与应对措施
2025.11.27 余苏 黄建城 刘晓欣
体育赛事的商业价值与传播热度持续攀升,带动版权交易金额屡创新高,但盗播侵权的阴影也随之蔓延。从过往电视台主导转播时的单一盗播行为,到如今网络时代聚合平台盗播、短视频片段侵权、主播嵌套式转播等多元侵权形态,侵权手段的技术化、产业化,让版权保护的难度与复杂度陡增,也给版权转播商带来了一系列亟待破解的法律问题。本文将聚焦体育赛事转播商视角,梳理有关法律规范、侵权类型、维权难点与解决路径。
一、体育赛事转播的有关法律规定
(一)著作权体系下的规定
体育赛事转播法律争议的起点在于“体育赛事节目是否构成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该认定直接锚定转播商的权利根基,也决定了后续版权保护的强度与边界。理论与司法实践中,关于赛事节目著作权属性的争议,长期聚焦于其应被界定为“视听作品”还是“录像制品”的核心分野。若被认定为“视听作品”,转播商可通过合法授权获得信息网络传播权、广播权、复制权等核心专有权利,有权针对盗播、片段剪辑等多元侵权行为主张权利;若仅被认定为“录像制品”,转播商仅能依托邻接权获得有限保护,难以覆盖复杂侵权场景。
从司法实践来看,法院对体育赛事节目是否构成作品已逐步形成明确的裁判导向。2020年以来的司法案例几乎均将体育赛事直播认定为视听作品。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3)京民申517号再审民事裁定书中,法院明确赛事直播画面通过镜头选择、画面切换、剪辑加工等创作行为,已具备著作权法要求的独创性,符合视听作品的构成要件。
(二)体育专项立法的规定
2022年修订的体育专项法规,从产业层面为赛事转播提供了基础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52条规定,未经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等相关权利人许可,不得以营利为目的采集或者传播体育赛事活动现场图片、音视频等信息。《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第25条将赛事转播权界定为“受保护的无形资产”,并禁止未经许可营利性传播赛事视听信息。前述规定在立法层面确立了赛事转播权的受保护地位,但就体育赛事节目的具体权利属性、相关法律后果缺乏明确界定,这一立法留白有待后续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填补。
(三)反不正当竞争法体系下的规定
当著作权保护存在认定争议或覆盖不足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成为赛事转播侵权维权的关键补充,常涉及的条款如下:
一般条款(第二条):该条款明确“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信的原则,遵守法律和商业道德”,不正当竞争行为即“违反本法规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例如,北京东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1民初22016号民事判决书中,被告以“主播解说属创新模式”抗辩,法院正是依据此条款,认定其“嵌套赛事画面+商业打赏”的行为违反公平诚信原则,构成不正当竞争。
混淆行为条款(第七条):禁止经营者实施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的混淆行为,包括“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等相同或者近似的标识”等情形。适用于侵权方通过仿冒正版平台标识、赛事专区名称等方式导流的场景,精准打击“搭便车”式竞争行为。
二、版权转播商面临的侵权类型
(一)完整盗播
完整盗播是指直接截取正版平台的赛事直播信号,通过自有网站、APP或客户端同步播放,不做任何修改,完全替代正版观看场景。例如,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的(2022)沪0115行保1号北京冬奥会赛事节目诉前禁令案中,某平台公司在2022北京冬奥会举办期间,未经许可通过其运营的“手机电视直播大全”软件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CTV5+等电视频道的方式,向公众提供2022北京冬奥会赛事节目的在线观看服务。
(二)片段化盗播
片段化盗播是指截取赛事核心片段(如进球、绝杀、争议判罚),经简单剪辑后快速传播,虽非完整内容,但形成“赛事精华”替代效应。例如,北京互联网法院(2024)京0491民初14331号案例中,被告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2022世界杯赛事期间未经许可通过其运营的“直播吧”APP对几乎每一场赛事节目大量以GIF格式视频及短视频的形式进行发布,发布时间与直播基本同步,且视频内容涵盖大部分赛事精彩画面。
(三)嵌套式盗播
嵌套式盗播常见是以“主播陪伴”“赛事点评”为幌子,在直播间嵌套播放正版赛事画面,叠加自身解说、打赏功能。出于举证难度、维权效率等考虑,在实践中这类案件通常通过不正当竞争追责。例如在北京东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1民初22016号案例中,某平台以“嵌套央视网页+主播实时解说+用户弹幕互动”的形式,全程、多路传播央视转播的奥运节目,并在百度投放“奥运会全程直播”等关键词商业推广,精准导流搜索奥运直播的用户。
三、版权转播商维权难点
(一)许可链条瑕疵
在体育赛事转播中常涉及多级授权,该场景下许可链条的完整性直接决定转播商维权的合法性,任一环节的协议瑕疵都可能成为侵权方的核心抗辩理由。例如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22)沪民申1878号民事裁定书中,A公司主张其通过“中国足协—体育之窗—排球之窗—A公司”的四级许可链条获得中超独家网络转播权,而B公司以“中视体育授权”为由转播,法院查明中视体育仅为摄制方、著作权归体育之窗所有,B公司的授权链条不完善且无证据表明B公司仅提供技术服务,最终判决B公司构成侵权。由此可见,若上游授权存在权利断层、范围模糊等瑕疵,即便支付高额版权费,也会在诉讼中陷入被动,甚至丧失维权基础。
(二)侵权证据固定难
盗播行为的“即时性、隐蔽性、跨区域性”特质,让证据固定成为维权又一道难关。侵权平台常通过动态切换盗播源、境外服务器跳转、加密传输等技术规避监测,加大了固定证据的难度与时间成本。即便针对境内侵权,短视频平台的片段化传播也增加了取证难度,侵权内容往往“传完即删、换号再发”,转播商需在短时间内完成内容抓取、权属比对与主体锁定等工作,对转播商的技术支撑和能力是一项巨大考验,往往容易出现证据缺失。
(三)对侵权平台的追责难
“技术中立”下,对平台追责存在一定难度。在“避风港规则”下,平台可根据《民法典》第1194、1195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主张自身仅提供技术服务,已履行“通知-删除”义务,不应承担责任。此外,侵权平台还可能以“提供信息存储空间”“链接跳转服务”为由,将侵权责任推给用户或上游盗播源,从而增加了对侵权平台追责的难度。当然,“避风港规则”也存在例外情形。根据《民法典》1197条的规定,当侵权事实像“红旗”一样明显时,即便没有权利人的通知,平台也需履行注意义务,否则不能免责。但即使存在例外情况,要对平台追责,法院也需结合平台是否对侵权内容进行算法推荐、是否参与广告分成、是否设置赛事内容专题等细节综合判定,这可能导致举证周期较长。
四、建议
(一)筑牢权利基础
版权转播商的权利主要依托许可合同授权,因此在合同审核当中可以注意以下事项:确保审核许可链条完整性,要求上游提供全链路授权文件,确保无断层;审核权利属性,明确赛事节目为“视听作品”并附著作权登记证书;审核维权授权,确认自身拥有独立起诉权,无需上游额外授权即可追责;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权利无瑕疵承诺”及违约赔偿条款写入合同,约定若因上游权利问题导致维权失利或损失,上游需承担全额赔偿责任。
(二)建立应对机制
在侵权应对层面,网络转播商需构建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采取不同措施打击侵权行为:事前搭建AI技术监测网等技术手段更加精准高效地发现与定位侵权事件;事中对核心赛事侵权考虑申请“诉前禁令”等措施及时止损;争议发生后可对不同侵权类型针对性主张权利,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同时主张著作权侵权与不正当竞争,同时可参照“网络影视反盗版联盟”通过合作共享关键资源与线索的实践,降低维权成本。
(三)探索合作策略
在赛事转播侵权维权成本高、诉讼结果不一定符合预期的情况下,可以尝试探索新商业策略,将侵权方转化为合作伙伴。例如主动与短视频平台达成分级授权协议,明确短视频剪辑、传播的权利边界。一方面可以收取版权费,另一方面可以引导短视频用户跳转至正版平台观看完整内容,为会员体系导流,推动实现多方共赢。
声 明
《君合法律评论》所刊登的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得视为君合律师事务所或其律师出具的正式法律意见或建议。如需转载或引用该等文章的任何内容,请注明出处。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转载或使用该等文章中包含的任何图片或影像。如您有意就相关议题进一步交流或探讨,欢迎与本所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