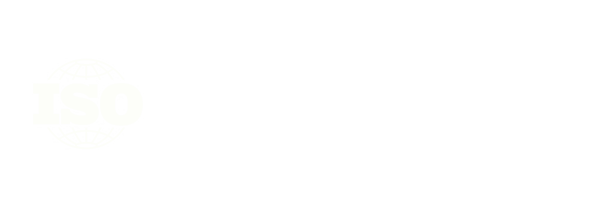参与亚行项目必看——深度解析亚行《调查与执法框架》的规则更迭和实践观察(下)
2024年10月21日,亚洲开发银行(下称“ADB”或“亚行”)颁布了《调查与执法框架》(Investigation and Enforcement Framework),取代了此前亚行于2005年颁布的《廉政指南和程序》(Integrity Guidelines and Procedures)和2015年颁布的《廉政合规指南》(Integrity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2015指南》”)。这是近十年来亚行对于调查与制裁不当行为规则的重大修改,是多边开发银行在推进合规事业发展上的又一亮点和重大突破。
作为多边开发银行调查与合规的专业团队,我们长期在一线参与各种不同类别的亚行、世行、非行等多边开发银行的调查、和解谈判、解除制裁和监管整改等相关合规业务。我们希望结合我们最近一年对《调查与执法框架》实施以来的实践观察,向正在面临相关调查或制裁压力的中国企业分享我们对《调查与执法框架》的认识和心得。
当然,亚行的调查与制裁程序还有很多丰富的实践内涵和外延,一到两篇文章并不能穷尽所有值得注意的细节,而避免或者减轻制裁的关键往往隐藏在很多“魔鬼”细节之中,对此可以进一步咨询我们君合的多边开发银行调查与合规专业团队。
此前,我们发布了本文《参与亚行项目必看——深度解析亚行《调查与执法框架》的规则更迭和实践观察》的上半部分(第一章至第三章),详情请见君合法评丨参与亚行项目必看——深度解析亚行《调查与执法框架》的规则更迭和实践观察(上);本次推送内容为本文的下半部分,详见如下:
四、暂停资格机制的完善
《调查与执法框架》对《2015指南》中规定的暂停资格机制作了进一步完善。
第一,在OAI申请暂停资格的基础上,IEC对于OAI暂停资格申请的审查标准在《调查与执法框架》中被明确,即应当遵循表面证据标准(on a prima facie basis);
第二,《2015指南》并未对被暂停资格的相关方如何提出异议进行详细规定。而《调查与执法框架》则在此方面进行了完善。相关方在收到暂停资格决定通知后,有 30 天的提出异议期限。如果相关方未在上述规定期限内提出异议,则其暂停资格应视为被确认;如果相关方在规定期限内向IEC提交了异议,IEC 应立即通知OAI其已收到异议,并给予OAI合理的期限回应异议。IEC在决定是否确认暂停资格时应考虑相关方的异议以及OAI的任何回应。在IEC审查期间,暂停资格决定应继续有效。
第三,暂停资格期间,合同变更须经OAI批准,并遵循《调查与执法框架》规定的程序。
此外,《调查与执法框架》进一步明确,在 ADB 非主权业务及 ADB 交易咨询服务中,ADB 将:
1. 不会在明知对方处于暂停资格状态的情况下,与其建立直接合同关系;
2. 可对处于暂停资格状态的相关方参与ADB 相关活动提出异议。在此情形下,ADB 可要求将该暂停资格方排除(参与范围),和/或采取其他风险缓解措施。
五、制裁机制的发展
(一) 执法措施的定义
在《2015指南》中,制裁措施被分为取消资格(Debarment),附解除条件的取消资格(Debarment with conditional reinstatement),附条件的不予取消资格(conditional non-debarment),并列明了其他补救措施(other remedial actions)包括训诫(Reprimand)、赔偿和/或补救(Restitution and/or remedy)以及警告(caution)。
《调查与执法框架》则定义了执法措施(Enforcement action)的概念,将取消资格、附解除条件的取消资格、附条件的不予取消资格、训诫(Reprimand)以及赔偿和/或其他经济补救(Restitution and/or other financial remedies)定义为执法措施。值得注意的是,警告(caution)并未被列为执法措施。
(二) 被制裁主体范围的进一步明确
《调查与执法框架》中对于被制裁主体的范围作出了进一步明确,以降低可能涉及被制裁行为的有关主体再次参与亚行项目的可能性。
1. 在被取消资格的主体中任职的人员
《调查与执法框架》规定,若被取消资格的主体为企业,该等取消资格将适用于该企业的管理人员、负责人及员工。除非这些人员已与被取消资格的主体完全脱离关系,否则无论是以个人身份,还是以未被取消资格的企业的名义,均不得参与亚行相关的活动。
这一规定体现了亚行进一步加强了取消资格措施的执法力度。我们理解,这一规定主要目的在于降低涉及被制裁行为个人再次以个人名义或其他公司名义参与亚行项目的可操作性。对于“与被取消资格的主体完全脱离关系”的标准,《调查与执法框架》并未进行明确,但考虑到亚行在其措辞中使用了“完全(completely)”一词,该等标准应当较高。
基于这一规定,任何拟参与亚行项目的个人应当在参与项目前(无论是以个人名义还是以其他公司名义),认真调查所在公司是否涉及取消资格制裁。此外,对于拟参与亚行项目的公司而言,应当确保所聘任的项目工作人员,尤其新近入职的、拥有其他公司工作经验的人员,其以前所任职公司并非被取消资格的主体,或者如是被取消资格的主体,所雇佣的该等人员也已经“与被取消资格的主体完全脱离关系”。
2. 其他与被取消资格主体有关的主体
《2015指南》规定,“为防止规避(制裁)行为,制裁措施通常将适用于控制该主体或受该主体控制的所有实体,包括该主体未来可能拥有主要受益权或控制权的实体。”
《调查与执法框架》则规定,为防止规避取消资格制裁的行为,取消资格通常将延伸适用于被取消资格主体所控制的所有主体,包括被取消资格主体后续获得主要受益权或控制权的主体。除此之外,如果有证据表明被取消资格主体的关联方曾参与违反廉政合规政策的行为,或从其中获益,则亚行的取消资格有可能延伸适用于:(a)控制被取消资格主体的主体;和/或(b)与被取消资格主体受共同控制的主体。在判定受益权或控制权时,应考虑相关因素,例如与被禁止参与主体的关联程度,以及与被禁止参与主体在业务活动或运营方面的相似性。
首先,对于“控制被取消资格主体的主体”是否应当被制裁的问题,《调查与执法框架》下,取消资格的向上穿透有了更清晰明确的前提条件,即能够证明该控制主体曾参与违反廉政合规政策的行为,或从其中获益。
其次,《调查与执法框架》也明确了被制裁主体的兄弟公司(即由同一公司共同控制的公司)是潜在的被制裁对象,其被取消资格前提也是该兄弟公司曾参与违反廉政合规政策的行为,或从其中获益。
此外,《调查与执法框架》特别强调了“在判定受益权或控制权时,应考虑相关因素,例如与被禁止参与主体的关联程度,以及与被禁止参与主体在业务活动或运营方面的相似性”,并列举了判定受益权或控制权时应考虑的相关因素,为取消资格的制裁和执法中的这一问题提供了指引。
(三) 制裁的公开披露规则
《调查与执法框架》沿用了《2015指南》下的“首次制裁不公开”原则,即通常情况下亚行并不会公开首次被取消资格者的名称。然而,在某些情况下, IEC或IEC主席可以决定公开披露对首次被制裁者的制裁。《调查与执法框架》规定“若基于机构层面的考量,即便涉及的是首次违规,相关禁止参与措施仍应对外公开。任何此类公开均须遵循《信息获取政策》及亚行的其他相关规则。”根据我们的经验,实践中,如果被调查对象首次违规行为性质特别严重或者被调查对象不配合亚行调查,可能会导致制裁公开。
六、解禁机制的完善
(一) 细化申请解禁的材料要求
通常而言,被处以取消资格或附条件恢复资格的取消资格的当事方,不会在指定的最短取消资格期限届满时自动恢复其参与亚行相关活动的资格。在《执法决定通知》(Notice of an Enforcement Decision)规定的最短取消资格期限届满后的任何时间,当事方可向OAI提交恢复资格申请(an application to OAI for reinstatement)。
关于恢复资格申请,《2015指南》规定须:
1. 以书面形式提交,致送OAI处长(the Director, OAI);
2. 说明受到制裁的原因;以及
3. 阐述亚行应考虑恢复其资格的依据。
而《调查与执法框架》则规定恢复资格申请须:
1. 采用书面形式,致送AIID处长(the director, AIID);
2. 证明其已完全遵守《执法决定通知》中规定的恢复资格条件;
3. 披露自《执法决定通知》发布日期起,该当事方是否受到其他国际金融机构或多边开发银行的调查和/或执法行动;及
4. 若被取消资格主体为公司,则需披露截至申请之日发生的以下任何情况:
(1) 公司管理层或所有权的变更;及
(2) 公司名称和/或地址的变更。
《调查与执法框架》对于提交恢复资格申请的要求进一步明确,反映出亚行对于被制裁主体在取消资格期间内变化的关注,也体现出亚行对于执法和解禁措施的掌控力度进一步加强。
(二) 明确当事方挑战OAI不予解禁决定只能向IEC申请
在当事方提交恢复资格申请后,OAI有权拒绝恢复资格,即不予解禁。
对于OAI若作出不予解禁的决定的情况,《2015指南》的有关规定为:
(1) 审查或调查结束后,OAI应决定是否恢复当事方资格。若OAI认定不应恢复某当事方资格,将准备报告提交IOC并提出相应建议。IOC可决定恢复其资格,或将制裁延长特定的最短期限(specified minimum time),在此期限结束后该当事方可再次申请恢复资格。
(2) 若IOC决定将制裁延长特定的最短期限,当事方可依据上诉程序向SAC对该决定提出上诉。
(3) 在特殊情况下,OAI可评估恢复某当事方资格或将其(包括被无限期取消资格者)从亚行宣布的无资格名单中移除的合理性。OAI仅可在为防止出现误判(miscarriage of justice)或避免亚行取消资格名单过时(obsolescence of ADB’s list of debarred parties)的情况下采取此项行动。
(4) 若当事方成功对决定提出上诉,或OAI认定制裁属于误判的情况,则该当事方的资格将获得恢复。
据此,《2015指南下》OAI有权基于司法不公来推翻不予解禁决定,从而让当事方恢复资格。
然而,《调查与执法框架》下则并未规定OAI有此权限。《调查与执法框架》规定,如OAI以被取消资格方未充分遵守有关解禁规定为由拒绝其恢复资格申请,该被取消资格方可向IEC提交申请,要求对OAI的决定进行复核。
若IEC同意OAI不恢复资格的决定,IEC可以:
(i) 将取消资格期限延长一个特定的最短时期,该当事方可在延长的最短期限届满后,依据有关规定再次申请恢复资格;或
(ii) 不延长取消资格期限。该当事方在符合有关解禁规定的要求后,可再次申请恢复资格。
IEC秘书处应及时将关于恢复资格申请的决定(包括该决定的依据,以及当事方向EAC提出上诉的权利)通知当事方和OAI。对IEC作出的不恢复资格的决定,当事方可向EAC提出上诉。
《调查与执法框架》在此方面的调整事实上限制了OAI在当事方挑战不予解禁决定时的权利。
一方面,《调查与执法框架》下OAI有单独的权力拒绝解禁申请(sole authority to deny),而在《2015指南》下若OAI认定不应恢复某当事方资格,应准备报告提交IOC并提出相应建议。这意味着《调查与执法框架》下OAI是拒绝解禁申请的第一决定人,再赋予OAI以推翻不予解禁决定的权力并无必要。
另一方面,对于OAI不予解禁的挑战理应全权由IEC和EAC这两个专门的审查与决定处理,因为IEC和EAC相对OAI而言对调查参与程度较轻,具有更高的中立性保障,同时也具有更高的专业性。
(三) 新增解除附条件不取消资格的相关程序
《2015指南》规定,就附条件不取消资格制裁而言,若被处罚方未能在规定期限内证明其已符合相关条件,则取消资格的制裁将自动生效,但《2015指南》并没有提及解除附条件不制裁的相关程序。
《调查与执法框架》对此事项作了明确规定:
1. 受到附条件不取消资格制裁的当事方,若自认为已满足解除制裁的特定条件,可在《执法决定通知》规定的"不取消资格转为取消资格"生效日期之前的任何时间,向OAI申请解除该执法行动。
2. 当事方向调查办公室提交的解除附条件不取消资格申请必须:
a) 采用书面形式,致送AIID处长;
b) 证明其已完全遵守《执法决定通知》中规定的解除条件;
c) 披露自《执法决定通知》发布日期起,该当事方是否受到其他国际金融机构或多边开发银行的调查和/或执法行动;及
d) 若当事方为公司,则需披露截至申请之日发生的以下任何情况:
(1) 公司管理层或所有权的变更;及
(2) 公司名称和/或地址的变更。
3. OAI将决定是否批准解除附条件不取消资格的申请,并及时将其决定通知当事方。
4. 若OAI因任何理由拒绝申请,该当事方可在《执法决定通知》规定的"不取消资格转为取消资格"生效日期前90天内的任何时间,再次向OAI提交解除附条件不取消资格的申请。
5. 若在《执法决定通知》规定的"不取消资格转为取消资格"生效日期,相关当事方未向OAI提交解除附条件不取消资格的申请,则通知中规定的取消资格期限及所有条件将自动开始生效。
6. 若在《执法决定通知》规定的"不取消资格转为取消资格"生效日期,当事方存在以下情况:
a) 已向OAI提交解除申请,但OAI尚未作出决定;或
b) 在OAI拒绝解除申请后,已向IEC申请复核,但IEC尚未作出决定;
则在此类决定作出之前,"不取消资格转为取消资格"的转换暂不执行。
7. 若OAI在"不取消资格转为取消资格"规定生效日期的前90天内拒绝解除附条件不取消资格的申请,相关当事方可向IEC提交申请,要求对OAI的拒绝决定进行复核。
8. IEC秘书处会及时将IEC关于解除申请的决定(包括该决定的依据,以及当事方向EAC提出上诉的权利)通知当事方和OAI。对IEC作出的不解除附条件不取消资格的决定,可向EAC提出上诉。
9. 因附条件不取消资格转换为取消资格而被制裁的当事方,可根据有关规定按取消资格方申请恢复资格的程序来申请恢复资格。
整体上而言,“解除附条件不取消资格的程序”与“解除取消资格的程序”十分类似。都是由OAI进行初步决定,当事方有权就OAI的否定性决定申请IEC再次审核,并可就IEC的决定向EAC申请上诉。
尽管存在前述的高度类似性,“解除附条件不取消资格的程序”仍然是具有高度价值的,是此次亚行规则革新的一大亮点。一直以来,“附条件不取消资格”的当事方对于如何申请解除制裁存在不确定性,此次规则的更新为有关当事方提供了明确的指引,使当事方有了准确的制度性依据。这也提醒遭受“附条件不取消资格”制裁的当事方应当及时、妥当地提起解除申请,以免被取消资格。
(四) 制裁期间合同变更的处理程序
相较于《2015指南》,《调查与执法框架》专门引入了针对处于取消资格或暂停资格期间合同变更的处理机制。相关当事方须将其受取消资格或暂停资格的情况告知项目执行机构(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且任何合同变更均需获得OAI的批准。当事方及项目执行机构向OAI提交合同变更申请,应在计划变更生效前留出合理时间提前进行。
OAI将从廉政合规角度审核拟议的变更,判断其是否存在规避现行取消资格或资格暂停的意图。若OAI认定该变更不涉及规避制裁行为,则会予以支持,并通知亚行相关执行部门。反之,若OAI认为该变更可能试图规避取消资格或暂停资格的约束,则将建议亚行不予接受,并立即告知相关部门。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若合同变更未获OAI批准而擅自实施,该行为可能被视为违反廉政规定(构成对亚行制裁的违背),并可能面临亚行开展的调查及后续执法行动。
(五) 新增从《取消资格及暂停资格登记册》中除名的相关程序。
《调查与执法框架》新增了从《取消资格及暂停资格登记册》中除名的相关程序(Removal from the ADB Debarment and Suspension Register)。
具体而言,在下列情况下,OAI可将某一当事方(包括被无限期取消资格者)从亚行《取消资格及暂停资格登记册》中除名:
1. 为避免亚行取消资格名单出现陈旧过时或冗余重复(obsolescence or redundancy)的情况;或
2. 当事方基于其继续列于取消资格名单缺乏合理性或比例性为由,向OAI提出除名申请并提供相应证明。
若OAI拒绝依据该除名请求,当事方可申请IEC对该决定进行复核。IEC作出的拒绝除名决定不得向EAC提出上诉。
此前,《2015指南》仅在取消资格解禁申请部分提及 “OAI仅可在为防止出现误判(miscarriage of justice)或避免亚行取消资格名单过时(obsolescence of ADB’s list of debarred parties)的情况下采取此项行动”,这句话虽然可以作为OAI在某些情况下将被制裁方恢复资格的依据,但缺乏明确规定导致其可操作性较弱。此次《调查与执法框架》将“从《取消资格及暂停资格登记册》中除名”作为单独一节进行规定,明确了OAI的有关权限,以及对于OAI决定的可上诉性,为更多试图申请恢复资格的当事方提供了尝试的机会以及相应的规则依据。
七、《调查与执法框架》颁布与实行的意义
(一) 制度体系全面优化,标志着亚行廉政合规治理进入新阶段
《调查与执法框架》系统性地取代了2005年《廉政指南和程序》与《2015指南》,它不仅意味着规则的更新,更是亚行廉政合规治理体系的重大升级。它广泛吸纳了近十年来多边开发银行在廉政合规领域形成的协调准则与国际最佳实践,并深度总结了亚行自身的执法经验。相较于《2015指南》,《调查与执法框架》在体例结构上更为完整,在内容上更为充实、具体,其可操作性与实用性显著提升。这标志着亚行建立了一个更为成熟、规范、透明的调查与制裁体系,是其廉政合规建设迈向新高度的里程碑。
(二) 机构职能与程序机制深度改革,提升调查执法的公正性、专业性与效率
《调查与执法框架》对亚行内部的制裁职责机构进行了重塑与强化,明确了OAI、IEC和EAC的职责分工与制衡关系。
1. 职能科学化:通过设立IEC和EAC分别作为一级和二级制裁机构,取代原有的IOC和SAC的职能,并明确其成员构成与独立性要求,进一步强化了制裁决策的专业性与中立性。
2. 程序精细化:引入了IEC主席对《调查结论函》的前置审查、独立的《质询函》程序、正式的和解程序等,既加强了对OAI调查权力的监督,也保障了被调查方的陈述与抗辩权利,体现了程序公正。
3. 权力与制衡并重:在赋予OAI更丰富的调查工具(如明确的信息共享权、细化配合义务)和更大裁量权(如签发不予追究通知、警示通知)的同时,也通过IEC和EAC的复核与上诉机制(如对于OAI拒绝解禁申请决定的复核与上诉)进行约束,构建了更为平衡的权力运行机制。
(三) 规则界定更为清晰精准,增强合规可预期性与风险防控能力
《调查与执法框架》对关键概念和行为标准进行了更精确的界定,为企业的合规实践提供了明确指引。
1. 明确行为边界:例如,将“利益冲突”本身不再直接定义为违规,而是强调“未披露且未采取合理措施管理”才构成违规,限缩了范围,提升了规则的准确性。
2. 完善责任体系:明确增加了“协助、教唆”等行为的责任,并细化了代理责任的适用条件,扩大了责任追究的覆盖面,同时也使责任认定更有依据。
3. 降低不确定性:对“妨碍行为”的定义从“包括”改为“系指”,并调整了具体构成要件,降低了认定门槛,但也使得边界更为清晰,减少了模糊地带。
(四) 权利救济与解禁渠道多元化,体现制裁的矫正与恢复功能
《调查与执法框架》显著加强了对被制裁方权利的保护,并建立了更为完善的回归路径。
1. 完善解禁机制:详细规定了申请恢复资格(解禁)和解除“附条件不取消资格”所需的具体材料与多级复核程序,为被制裁方提供了明确、可操作的“改过自新”路线图。
2. 新增除名程序:首次明确了可将当事方从《取消资格及暂停资格登记册》中除名的情形和程序,为解决名单“过时”、“冗余”或特定不公情形提供了制度出口。
3. 挑战决定路径清晰:明确了对OAI不予解禁等决定,当事方可向IEC申请复核,并可进一步上诉至EAC,确保了权利救济渠道的畅通。
(五) 实践导向突出,强化对项目执行与风险防控的全过程管理
《调查与执法框架》针对实践中的难点与风险点,新增了关键操作程序,增强了事中事后监管。
1. 新增合同变更审查:明确规定在制裁或暂停资格期间,合同变更需经OAI事前批准,有效防止了通过变更合同规避制裁的行为,堵住了制度漏洞。
2. 强化企业配合要求:细化了被调查方的配合义务清单,并明确不配合可能导致不利推定,促使企业在调查中采取积极合作态度,同时也为OAI开展深入调查提供了有力支撑。
总结而言,《调查与执法框架》的价值与意义在于,它通过系统性的制度重构、精细化的程序设计、清晰化的规则界定、人性化的权利保障和导向性的风险管控,共同推动亚行的廉政合规体系迈向更高水平的制度化、规范化和透明化。对于企业而言,这既是更为严格的合规挑战,要求其必须深入理解新规、全面加强内控;也是一个更清晰的合规指引,为其应对调查、申请救济、实现合规回归提供了明确的规则依据,最终将有助于营造亚行项目中更加公平、廉洁、健康的商业环境。我们也期待将来能有更多的实践体悟和读者分享。
* 本文首发于《君合大合规业务月报》
2025年10&11月刊
声 明
《君合法律评论》所刊登的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得视为君合律师事务所或其律师出具的正式法律意见或建议。如需转载或引用该等文章的任何内容,请注明出处。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转载或使用该等文章中包含的任何图片或影像。如您有意就相关议题进一步交流或探讨,欢迎与本所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