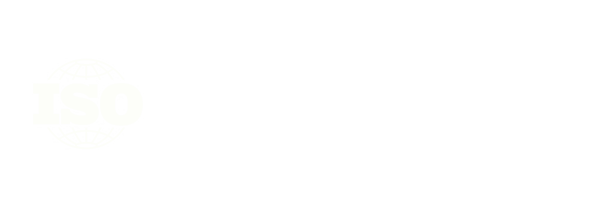高校聘用制教师“非升即走”合同引发的解聘纠纷案件
2025.09.03 余苏 张美怡
前言
公立高校聘用制教师“非升即走”的条款在国内高校专任教师聘用中逐渐普及,并在近年多次成为舆论热点话题。2025年8月,有公开报道指出广东地区有年仅41岁的高校教师疑似因未通过“非升即走”考核而选择终结生命;在此前半个月,浙江地区一名35岁博士后同样疑似因考核压力跳楼离世,令人惋惜。常见的“非升即走”条款模式是,高校与教师约定在某个固定期限(例如5年)内,教师须晋升到上一等级的专业技术职务(例如从讲师晋升副教授),否则高校将解除聘用关系。一方面,“非升即走”的聘用机制成功激活学术生产力,解决高校“尸位素餐”痛点,优化了人才结构;但另一方面,部分教师由于受到职称考核与聘用挂钩的压力,被迫重科研而轻教学,追逐“短平快”的学术热点,导致有人诟病“非升即走”导致科研量产化;与此同时,“非升即走”模式下的激烈竞争1也难免引发对高校与教师之间关系紧张的忧虑。在法律界,“非升即走”聘用制度已不乏学术讨论2,而值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在2025年8月1日最新发布之际,我们本次从上海地区法院裁判的一起人事争议案件一窥法院对“非升即走”合同条款的司法观点。
案例分析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3)沪0115民初126387号案中,原告殷某于2015年入职上海某高校法学院担任专任教师,2023年被告高校以新聘教师科研考核不合格为由,通知自8月起终止与原告的聘用关系。原告以违法解除聘用合同为由,起诉被告要求恢复聘用关系,理由包括:(1)被告在原告入职前后未告知有新进教师科研考核要求;(2)被告在2022年3月违法二次认定原告科研考核不合格;(3)被告在终止聘用关系上明显违反事业单位人事管理规定,解聘时仅支付1个月代通知金,未支付经济补偿。
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于2015年8月18日入职被告处,系事业单位聘用制人员,与被告人事处累计签订两份聘用合同,约定原告在被告下属法学院担任讲师,聘用期限分别为2015年8月18日至2018年12月31日及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其中第二份聘用合同附件中载明聘期工作任务目标为达到被告学校制度关于聘任副教授的教学及科研等指标要求。2022年3月2日法学院召开党政联席会议原告进行了考核,决定如下:1、原告未到达续聘期考核合格标准,法学院给出的考核意见为:不合格……。”2021年下半年新聘教师总聘期考核情况汇总表(6年)中“论文论著发明专利”“科研项目”栏,原告均为“无”。
2022年7月16日、2022年9月20日以及2022年11月14日,被告人事处分别向原告发送电子邮件,告知根据被告学校制度相关规定,经学院考核和学校审定后,原告的续聘期考核为不合格,结合原告个人选择,经研究决定,原告可待转岗一年,待转岗期限为一年,待转岗期限为2022年8月1日至2023年7月31日,待转岗期限满,若未被聘岗,学校与原告的聘用关系于2023年7月31日终止,聘用关系终止后不再续聘。2023年7月5日,被告人事处向原告发送《通知》,内载:“您的待转岗期限将于2023年7月31日结束,学校与您的聘用关系将于2023年7月31日终止,聘用关系终止后不再续聘”。
基于以上查明事实,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聘用合同书》期限至2021年12月31日届满,被告依照规定对原告进行续聘期考核,经考核,原告考核结果为不合格。原告如对考核结果有异议,可以按照规定申请复核、申诉。但之后经过沟通,原告选择“待岗一年”。现基于待转岗期限满已于2023年7月31日届满,原告仍未被聘岗,故被告于2023年7月31日终止与原告聘用关系并无不当。据此,法院驳回了原告要求与被告恢复聘用关系的诉讼请求。
虽然该案的诉讼请求处理较为简单,但是法院处理思路在以下方面值得关注:
(一)“非升即走”合同下的法律关系
本案中,被告为事业单位,原告系事业单位实行聘用制的人员。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3、《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六条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5,在程序方面,高校解聘在编教师适用“协商→调解→仲裁→民事诉讼”一般劳动争议处理程序;在实体方面,事业单位与实行聘用制的工作人员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除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劳动合同法》有关规定执行。因此,本案法院依照劳动合同的审理路径进行审理。
在本案中,法院并没有对原告提出的考核异议进行审理,可以理解为法院将高校的职称评审行为视为高校内部正常管理活动,不属于法院的受案范围与审理范围,不具有可诉性。因此,只有“聘用”“解聘”行为才能被纳入民事诉讼的范围;对于“评审”的异议,教师需按照《人事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申请复核、提出申诉。
(二)“非升即走”条款的性质是附解除还是附期限?
“非升即走”属于“附解除条件”还是“附期限”的合同,不同性质决定了不同的处理逻辑。如果将“非升即走”解释为合同的解除条件,则根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不得在《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6规定的劳动合同终止情形之外约定其他的劳动合同终止条件,显然该等所附条件并无法律依据。而在本案中,法院实际上是依循原被告双方的约定的聘用合同起止期限,认定劳动关系的终止在于原告转岗期限的届满,因此没有落入《劳动合同法》禁止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以外其他劳动合同终止条件的禁区。
(三)引申问题: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后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订立劳动合同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三)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劳动者没有本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续订劳动合同的。”过去的劳动案件司法实践中,不同地区法院对该条的理解适用存在一定差异:多数地区的法院认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劳动者没有该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只要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订立劳动合同的,则用人单位无选择权,应当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本案所在的上海地区法院则认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连续签订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后,用人单位仍有权选择是否与劳动者续订第三次劳动合同,如用人单位无续订意愿的,则劳动者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前提条件不成就。该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用人单位更多的自主权,确保劳动合同的签订系基于双方双向选择的结果。
但是,在2025年8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新闻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宜芳在发言中指出:《解释二》立足以高质量审判促进稳就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是引导用人单位更好履行稳岗社会责任。劳动合同短期化问题易导致劳动关系不稳定,既不利于劳动者就业,也不利于用人单位发展。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规定,在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不存在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因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及“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情形时,用人单位不得拒绝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要求。据此,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统一口径的情况下,上海地区司法观点很可能发生转变,与全国其他多数地区的司法口径保持一致,即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连续签订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后,只要劳动者符合续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条件,劳动者即具有单方选择权,用人单位无权拒绝续订劳动合同。
回归本案,一个值得关注的特别情形是,原告作为聘用制教师已与被告高校签订了两份固定期限聘用合同,在第二份固定期限合同到期之后,若原告拒绝转待岗而提出按照原岗位、原聘用条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那么在当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已发布并将于2025年9月1日施行的背景下,高校再以第二份固定期限聘用合同约定了“非升即走”条款为由不再与教师续聘将不在可行。同时,此情况下高校对教师的“评审”如何与《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二)项“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衔接,也值得进一步关注和思考。
结语
除另有特殊规定以外,高校与教师之间的聘用合同争议仍遵循一般的劳动争议处理程序。但是,司法实践中往往会区分针对“评审”的争议和“聘用”“解聘”的争议,前者属于学校的内部管理程序,一般不属于法院审理范围,但高校应当建立完整的评审或复核机制,保证过程的合规性;后者属于学校与教师之间的人事争议,除另有特别规定外,依照《劳动合同法》处理。而对于“非升即走”条款,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仅能视为约定了聘用合同的固定期限,而不应被视为约定的终止条件,因此,若双方仅签订了一份固定期限聘用合同,在聘期届满未达标者,高校依照《劳动合同法》约定有权不予续聘,但须参照《劳动合同法》第46-47条支付法定经济补偿金;而若双方在连续签订了两份固定期限聘用合同之后,若第二份合同触发“非升即走”条款,则即便高校按照学校制度评审教师为不合格,也需要依照《劳动合同法》规定满足“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情形,方可解聘,否则若仅因没有达到约定的专业技术职务上升要求就不再续聘,则可能引发违法解聘的人事争议。
1. 2018年9月,武大有69位聘期制教师首个聘期结束,校方统一组织了转编评审,42人仅有4人过关。参见张笛扬,李霁:《武大聘期制改革,转编评审淘汰率超九成——打破高校“铁饭碗”之后》,载《南方周末》2019年1月24日。
2. 参见:(1)徐靖:《高等学校“非升即走”聘用合同法律性质及其制度法治逻辑》,载《中国法学》2020年第5期,第44-63页;(2)刘旭东:《我国高校“非升即走”制度的困境研判及规范理路——基于《教师法(征求意见稿)》修订内容的研究》,载《教育发展研究》2022年第5期,第53-60页;(3)范奇:《高校教师“非升即走”制度探析——基于程序正义理论视角》,载《教师教育学报》2024年第5期,第91-103页。
3.《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与所在单位发生人事争议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有关规定处理。
4.《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六条:事业单位与实行聘用制的工作人员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未作规定的,依照本法有关规定执行。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处理。
6.《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终止:(一)劳动合同期满的;(二)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三)劳动者死亡,或者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或者宣告失踪的;(四)用人单位被依法宣告破产的;(五)用人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用人单位决定提前解散的;(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声 明
《君合法律评论》所刊登的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得视为君合律师事务所或其律师出具的正式法律意见或建议。如需转载或引用该等文章的任何内容,请注明出处。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转载或使用该等文章中包含的任何图片或影像。如您有意就相关议题进一步交流或探讨,欢迎与本所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