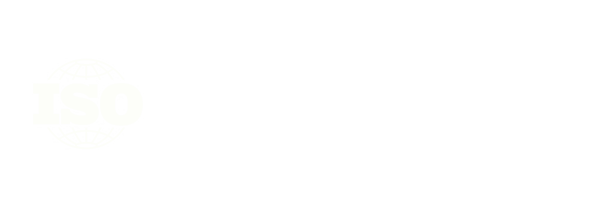关键词隐性使用合法性谜题未解 —— 新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第2款的适用讨论
2025.07.11 张传磊 顾劭宇
2025年6月27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称“新《反法》”)。新《反法》自2025年10月15日起施行。此次修订存在诸多值得关注的亮点,其中第七条针对关键词搜索行为新增规定:“擅自将他人注册商标、未注册的驰名商标作为企业名称中的字号使用,或者将他人商品名称、企业名称(包括简称、字号等)、注册商标、未注册的驰名商标等设置为搜索关键词,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的,属于前款规定的混淆行为”。
新《反法》的此处修改并非凭空出现,而是对互联网领域一直高频出现且饱受争议的关键词搜索行为之法律定性问题的回应。由于修订前的《反法》并未对此类问题作出直接规定,关键词搜索行为是否能定性为商标侵权、不正当竞争行为及其应定性为哪类不正当竞争行为一直在学术界及司法实践中存在分歧。此次新法虽然以立法形式对关键词搜索行为进行规定,但此次修改是否能化解关键词使用的定性争议,尤其是关键词隐性使用是否属于《反法》第七条的规制范畴,值得探讨。本文将围绕关键词隐性使用问题,结合过往的立法动态和司法实践,试对此次新法修改内容进行剖析:
一、关键词隐性使用的基本介绍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电子商务、大数据等行业的发展,当下公众通过网络获取特定信息、选购商品或服务已经成为常态;高效、快速地在海量信息中查询自己需要的信息已经成为公众普遍的需求。在前述大背景下,各网络运营商及服务平台一方面为公众提供可以通过搜索特定关键词来匹配特定信息的搜索引擎工具,另一方面也在向经营者提供搜索关键词竞价排名广告服务。这种广告服务允许经营者通过购买特定关键词搜索结果中的广告推送位置,将他人享有商标权或包含他人字号等内容的关键词作为触发因素,从而实现将经营者自身(甚至可能与前述关键词无关)的网站、广告链接展示在前述关键词的搜索结果中,以便对该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务进行推广宣传。
关键词竞价排名广告对于商业标识的使用目前普遍被区分为“显性使用”和“隐性使用”两种类型。在“显性使用”场景中,经营者购买特定关键词(如他人企业字号或商标等)后,用户搜索该关键词得到的结果中会出现前述经营者的广告内容和/或相关链接,且该等内容/链接上使用了前述关键词。由于显性使用行为已然普遍被认为很可能构成商标侵权和/或不正当竞争行为,因此越来越多的商家开始转向“隐性使用”行为,即仍将特定关键词(如他人商标、企业字号等)设置为与其链接关联的推广关键词,但仅将其在后台予以设置,而搜索结果中呈现的链接中并不展示该关键词。
相较于显性使用,由于隐性使用仅将特定关键词设置在后台,不构成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性使用”,因此司法实践中一般认为其不构成商标侵权。但是,隐性使用行为仍可能与关键词权利人之间存在抢夺流量及潜在交易机会等问题,权利人据此可能认为行为人攫取了权利人的商业利益。这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系列有关关键词隐性使用行为的民事纠纷案件。
二、关键词隐性使用的合法性争议
在新法修订前,《反法》(2019年修订)的规定并未直接包含关键词搜索行为。司法机关在涉及关键词隐性使用的案件中援引的法条主要包括《反法》(2019年修订)第二条和第六条。
(一)关键词隐性使用是否违反《反法》(2019年修订)第六条的争议
《反法》(2019年修订)第六条系对混淆行为的规制,该条规定:“经营者不得实施下列混淆行为,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一)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等相同或者近似的标识;(二)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影响的企业名称(包括简称、字号等)、社会组织名称(包括简称等)、姓名(包括笔名、艺名、译名等);(三)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域名主体部分、网站名称、网页等;(四)其他足以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的混淆行为”。可见,《反法》(2019年修订)第六条要求涉案行为满足 “足以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的构成要件。司法实践中,对于隐性使用行为是否足以引起公众的混淆误认,存在着不同的声音:
有的判决认为,隐性使用行为能够引起公众的混淆误认,并进而认定隐性使用行为构成《反法》(2019年修订)第六条以及规定的混淆行为。例如,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在“高佣”案中认定:“虽然知买公司的涉案APP仍处于搜索结果前部,但因搜索结果页面并未对呈现的德利微公司涉案APP予以特别注明,加之两款APP在名称及图标LOGO底色装潢部分存在混淆性近似,相关公众势必产生对应用APP服务来源或服务提供主体之间存在特定关系的混淆误认”1。但需要注意的是,该案件中法院认为隐性使用行为能够引起公众的混淆误认是有特殊性的,即“两款APP在名称及图标LOGO底色装潢部分存在混淆性近似”。
有的判决则不认为隐性使用行为会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例如,在“海亮”案中,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就认为:“随着搜索引擎行业的发展及其盈利模式的成熟,搜索网站的竞价排名现象已越来越为一般的网络用户所知晓,因此当输入含‘海亮’关键词后即使出现了上诉人网站,在推广内容未涉及‘海亮’的情况下,相关公众并不会因此就混淆服务来源或认为两者存在关联,而是会根据两者分别提供的信息和服务,进行理性的比较和选择”。2
需要说明的是,《反法》(2019年修订)第六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认为是对部分符合条件的未注册商标(商业标识)的补充保护,因此此前实际上大多数案件的原告还是会选择主张商标权,仅会在无法主张商标权时退而备位主张《反法》(2019年修订)第六条的保护。如前所述,对于隐性使用是否构成商标侵权,司法实践中普遍认为该等使用行为难以符合《商标法》对于“商标性使用”的要求。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隐性使用而言,似乎也不存在适用《反法》(2019年修订)第六条的基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司法解释》”)第十条规定:“在中国境内将有一定影响的标识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规定的‘使用’”。这与《商标法》第四十八条对于“商标性使用”的定义,即“本法所称商标的使用,是指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是一致的。上述观点亦可以获得司法判决的支持,例如,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在“贯信”案中就认为:“根据贯信公司提交的时间戳证据、百度公司提交的第3066号公证书及欧睿公司陈述,可确认欧睿公司仅在百度网后台添加了涉案关键词用于其网站的商业推广,但涉案推广链接的标题及描述中均未出现‘贯信’或‘上海贯信’字样。此种情形下,相关公众无法直接接触后台关键词,无法将涉案关键词与欧睿公司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相联系,故被诉行为并非标识性使用行为,缺乏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第二项之前提,本院对贯信公司该项主张不予支持”。3
(二)关键词隐性使用是否违反《反法》(2019年修订)第二条的争议
在无法通过《反法》(2019年修订)第六条规制隐性使用行为的情况下,有的关键词的权利人会同时寻求通过《反法》(2019年修订)第二条的救济。该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所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行为”。但是,就隐性使用行为是否构成该款规定的“一般性不正当竞争行为”,司法实践中的意见也并不同意,甚至存在更多的争议。
有的判决认为隐性使用行为构成“一般性不正当竞争行为”。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海亮”案中再审认定:关键词隐性使用行为利用了关键词本身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将原属于该关键词的流量吸引至自身网站,提高了自身网站的曝光率,从而获取竞争优势,亦造成了关键词权利方竞争利益的损害;“隐性使用”的行为对网络用户造成了信息干扰,增加了搜索成本,同时亦妨碍了搜索引擎基本功能的正常发挥。4又如,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在“贯信”案中就针对置顶的隐性使用行为认为:“根据一般用户的浏览习惯,在两条链接指向的服务内容近似时,其通常会选择点击排名靠前的链接,从而使得部分原本希望获取贯信公司产品信息的用户转而点击涉案推广链接进入涉案网站并最终购买欧睿公司产品”,并指出:“欧睿公司实施被诉行为系在未付出相应经营成本的情况下,将部分原属于贯信公司的用户引导至涉案网站,攫取了本属于贯信公司的潜在交易机会”“对于购买搜索引擎商业推广服务的经营者而言,即便仅在搜索引擎平台后台设置关键词,亦不能设置明显与其无关的他人商标或企业名称等关键词,否则即系恶意攀附他人经营利益而获得不应尤其享有的用户流量”。5
有的判决则不赞成隐性使用行为构成“一般性不正当竞争行为”。例如,江苏省高院在“金夫人”案中认为,该案中非置顶性的隐性使用行为并未使相关公众产生混淆误认,也未误导消费者,且商业交易机会并非法定权利。6又如,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在“URL”案中指出:通过使用他人商业标识作为关键词,使用人能够借助搜索引擎的服务实时的捕捉到哪些互联网用户在对竞争对手的商品或服务感兴趣,当这些消费者出现时,搜索引擎会即时地将使用人的网址链接呈现在这部分消费者面前;这是一种以“竞争对手的目标消费者群体的信息”为客体的交易,是一种帮助广告商定位到竞争对手的目标消费者群体的服务;这种关键词选用行为本身,是一种市场竞争的手段;在开放的竞争环境下,隐性关键词的使用方式符合现代销售和合法竞争的精神,该竞争行为并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7
总的来看,隐性使用是否构成《反法》(2019年修订)第六条规定的混淆行为?如不构成混淆,是否可以援引《反法》(2019年修订)第二条予以规制?对于这两个问题,尤其是适用上述第二条时会论及的“交易机会”是否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对象和客体,当下的司法实践并没有形成共识,而且呈现出较大的争议。这就需要平衡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法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将问题上升到了立法的高度。
三、关键词隐性使用的立法分析
如前所述,本次修订之前的《反法》并未直接包含有关关键词搜索的规定。而随着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及隐性使用行为的普及,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中出现了与搜索关键词有关的规定。例如,2020年修订的《上海市反不正当竞争条例》第八条第三款规定:“经营者不得通过将他人有一定影响的标识与关键词搜索关联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实施混淆行为”。又如,2024年9月1日起施行的《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第七条第二条规定:“擅自将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业标识设置为搜索关键词的,足以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的,属于前述规定的混淆行为”。从条文规定来看,上述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均试图将设置搜索关键词的行为纳入“混淆条款”规制的范围,并将“混淆可能性”作为构成要件,而非将“设置搜索关键词”一概规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
此次新《反法》第七条的形成过程,可能同样体现了这一趋势倾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022年11月22日发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七条第一款第(四)项为:“经营者不得实施下列混淆行为,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四)擅自将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业标识设置为搜索关键词,误导相关公众”。全国人大常委会2025年1月23日发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七条第一款第(五)项则调整为:“经营者不得实施下列混淆行为,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五)擅自将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企业名称(包括简称、字号等)等设置为其搜索关键词”,明确“商业标识”包括“商品名称、企业名称(包括简称、字号等)”,但是删除了“误导相关公众”的限定。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中载明:“修订草案第七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经营者不得擅自将他人注册商标、未注册的驰名商标作为企业名称中的字号使用,不得擅自将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企业名称(包括简称、字号等)等设置为其搜索关键词。有的部门、全国人大代表、地方和企业提出,这两项规定的行为是否属于混淆类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宜一概而论,为避免这两项规定在实践中被滥用,建议明确这些行为只有‘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的’才属于混淆类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采纳这一意见,并将这两项合并为一款作相应修改”。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修改意见的报告中载明:“有的常委委员提出,经营者将他人注册商标、未注册的驰名商标设置为搜索关键词导致混淆的情况也比较普遍,应当对这种情形予以明确。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将‘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企业名称(包括简称、字号等)’修改为‘商品名称、企业名称(包括简称、字号等)、注册商标、未注册的驰名商标’”。经过上述多次完善,最终通过的新《反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擅自将他人注册商标、未注册的驰名商标作为企业名称中的字号使用,或者将他人商品名称、企业名称(包括简称、字号等)、注册商标、未注册的驰名商标等设置为搜索关键词,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的,属于前款规定的混淆行为”。
通过回顾上述立法过程可见,新《反法》第七条关于“搜索关键词”的规定,均是在“混淆行为”的框架下进行的讨论。由此产生的问题是,是否存在混淆性的关键词隐性适用,以及非混淆性的关键词隐性使用行为是否还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需要强调的是,新《反法》第七条是关于“混淆行为”的规定,特别是结合上述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中“建议明确这些行为只有‘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的’才属于混淆类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内容,至多只能得出不存在混淆可能性的关键词隐性使用行为不构成新《反法》第七条规制的混淆行为的范畴。但是,对于下列两个问题,新《反法》第七条事实上并未直接予以回应:一是因为关键词隐性使用行为而可能受到影响的“交易机会”是否属于《反法》保护的利益?二是非混淆性的关键词隐性使用行为是否会受到新《反法》第二条的规制?
新《反法》第七条作出如此立法安排,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法律适用的进一步“撕裂”。《反不正当竞争法司法解释》第一条规定:“经营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合法权益,且属于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章及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规定之外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予以认定”。依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只有没有被知识产权专门法和《反法》第二章类型化的行为,才可以适用《反法》第二条的规定。对此可能存在的争议是,如何解读这里的类型化?具体到关键词隐性使用问题来说,是隐性使用不构成混淆行为,所以无需再适用《反法》第二条再行评判?还是隐性使用虽然不构成混淆行为,但是仍可以适用《反法》第二条进行评判?无论是新《反法》还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司法解释》本身,都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相关司法实践也并未就《反不正当竞争法司法解释》第一条如何适用形成一个明确的意见。这可能仍需留待司法实践进行回应。
四、余论
“将他人的商业标识设置为搜索关键词”已经成为新《反法》予以类型化的行为,但是该种行为的合规边界目前并不清晰,特别是非混淆性的关键词隐性使用行为是否仍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尚不能从新《反法》的条文本身得出结论,可能还需留待未来的司法实践去回应。对此,笔者认为,在立法机关无疑知晓关键词隐性使用可能包括“混淆性”和“非混淆性”两种情况的背景下,新《反法》对“非混淆性隐性使用”的“留白”,是否意味着立法层面认为该种隐性使用并不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一问题期待未来的立法和司法实践能够予以验证和回应。
1.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20)浙0110民初19778号民事判决书。
2.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浙民终463号民事判决书。
3.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8民初35597号民事判决书。
4.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民再131号民事判决书。
5.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8民初35597号民事判决书。
6. 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苏民申2676号民事裁定书。
7. 参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5民初3814号民事判决书。
声 明
君合官网所刊登的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得视为君合律师事务所或其律师出具的正式法律意见或建议。如需转载或引用该等文章的任何内容,请注明出处。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转载或使用该等文章中包含的任何图片或影像。如您有意就相关议题进一步交流或探讨,欢迎与本所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