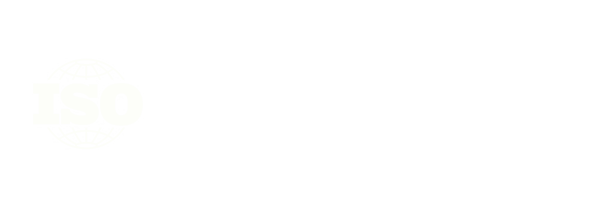江歌案法律评析:寻求法律下的正义
1970.01.01 王利华
近日,原告江秋莲(受害人江歌之母)诉被告刘鑫生命权纠纷案一审民事判决作出,且刘鑫已经上诉。在社会舆论对一审判决的高度赞扬中,也存在一些反对的声音1。在此情形下,笔者依据互联网上的一审民事判决书、律师代理词2等对该案进行法律分析与研讨。
一、缘起—江秋莲的诉讼思路与法院审判思路之辨析
江秋莲在中国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城阳法院”)以生命权纠纷起诉本案,其诉讼思路在于本案属于生命权纠纷民事侵权案件,江秋莲从过错、因果关系等论述了杀人者陈世峰与刘鑫构成共同侵权,其中刘鑫存在重大过错,是导致江歌落入险境造成遇害的前提与根本原因,同时刘鑫的侵权损害行为与江歌遇害存在因果关系,刘鑫的侵权损害行为是江歌遇害发生的前提与基础条件,进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8条,要求陈世峰与刘鑫对江歌之损害承担连带责任。
依据(2019)鲁0214民初9592号民事判决,法院总结该案的争议焦点之一刘鑫对江歌的死亡应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城阳法院认为该案是属于生命权纠纷民事侵权案件,刘鑫与江歌形成一定的救助关系,且刘鑫对侵害危险具有更为清晰的认知,因刘鑫未充分尽到注意义务及安全保障义务,故刘鑫应该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江秋莲的诉讼思路
法院审判思路
案由
生命权纠纷
生命权纠纷
侵权
共同侵权
侵权、救助关系、注意义务、安全保障义务、民法原则
构成要件
重大过错、共同侵权行为、有因果联系、经济和精神损失
过错、救助关系、未尽到注意义务、安全保障义务
经济损失
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签证费等各项经济损失1770609.33元
死亡赔偿金1118100元、丧葬费38164元、处理丧事误工费31786元、交通费19437元、住宿费30600元、签证费2192元,共计1240279元,法院酌情确定为496000元。
精神损失
精神损害抚慰金30万元(侵权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案件发生后持续的恶意伤害)
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人格权受损所致的精神损害赔偿+事后的刺激性言论)
二、问题的提出
显然,城阳法院并没有采纳江秋莲方关于共同侵权的观点,而是绕开共同侵权的问题,走向了救助关系、安全保障义务及注意义务。纯从法律技术角度,以共同侵权的思路论理更加直接,法律依据更加充分,而以救助关系为基础的安全保障及注意义务,更体现法官个人的理解,也导致了被质疑“道德审判”的风险3。但城阳法院舍近求远,必然有其内在原因。
共同侵权的构成要件为侵权主体的复数性、共同实施侵权行为、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受害人具有损害,且损害具有不可分割性4。本案中,江秋莲主张陈世峰与刘鑫构成共同侵权:第一、陈世峰与刘鑫系两人以上,构成侵权主体的复数,同时受害人江歌具有明显损害,且损害不可分割,此处不存在争议;第二、争议较大在于共同实施侵权行为和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江秋莲主张“二人在客观上有共同的侵权行为,并且形成了特殊的意思联络甚至于可以说是合意,即刘鑫希望陈世峰转移杀害目标至江歌身上时,陈世峰最终也将杀人目标定格在江歌身上并导致了江歌的死亡”,江秋莲在此采用了“意思联络说”、“共同行为说”,认为陈世峰与刘鑫有意思联络,即共同故意,使主体的意志统一为共同意志,使主体的行为统一为共同的行为,陈世峰与刘鑫共同实施了加害行为。本案中,陈世峰与刘鑫存在感情冲突,刘鑫是陈世峰的直接报复对象,要确定陈世峰、刘鑫有共同伤害或杀害江歌的意思联络相当困难。
回到陈世峰与刘鑫各自的具体行为看双方主观状态。
时间
陈世峰之行为
刘鑫之行为
2016年7月起至10月
刘鑫与陈世峰多次因琐事发生争执,陈世峰两次对刘鑫跟踪纠缠并寻求复合,刘鑫均予以拒绝。
另刘鑫因被陈世峰赶走,所以在江歌租住公寓内暂住,后刘鑫与陈世峰和好并回到陈世峰的住所同住。2016年9月2日起,刘鑫搬进江歌的住所。
2016年11月2日
1、当日15时许,陈世峰找到刘鑫与江歌同住的公寓,上门进行纠缠滋扰。
2、后在途中继续跟踪刘鑫,并向刘鑫发送恐吓信息,称要将刘鑫的不雅照片和视频发给其父母。
3、刘鑫到达打工的餐馆后,陈世峰从刘鑫处得知刘鑫有新男友及拒绝复合后愤而离开,随后又向刘鑫发送多条纠缠信息,并两次声称“我会不顾一切”。
1、刘鑫未打开房门,通过微信向已外出的江歌求助。江歌提议报警,刘鑫以合住公寓违反当地法律、不想把事情闹大为由加以劝阻,并请求江歌回来帮助解围。
2、当日16时许,江歌返回公寓并将陈世峰劝离,随即江歌返回学校上课,刘鑫去往餐馆打工。
3、刘鑫到达打工的餐馆后,为摆脱陈世峰的纠缠,求助一名同事充当男友,再次向陈世峰坚决表示拒绝复合。
4、期间刘鑫未将陈世峰纠缠恐吓的相关情况告知江歌。
2016年11月2日19时许至11月3日零时许
1、陈世峰返回住处,随身携带了一把长约9.3厘米的水果刀,准备了用于替换的衣服,并到附近超市购买了一瓶威士忌酒,随后赶到江歌租住的公寓楼内,在二楼与三楼的楼梯转角处饮酒并等候。
2、11月3日零时许,刘鑫、江歌前后进入公寓二楼过道,事先埋伏在楼上的陈世峰携刀冲至二楼,与走在后面的江歌遭遇并发生争执。走在前面的刘鑫打开房门,先行入室并将门锁闭。
3、陈世峰在公寓门外,手持水果刀捅刺江歌颈部十余刀,随后逃离现场。
1、11月2日23时许,江歌联系刘鑫询问陈世峰是否仍在跟踪。刘鑫回复称,没看见陈世峰,但感觉害怕,要求江歌在附近的地铁站出口等候并陪她一起返回公寓。
2、11月3日零时许,二人在地铁站出口汇合并一同步行返回公寓,二人前后进入公寓二楼过道,事先埋伏在楼上的陈世峰携刀冲至二楼,与走在后面的江歌遭遇并发生争执。
3、走在前面的刘鑫打开房门,先行入室并将门锁闭。
4、刘鑫在屋内两次拨打报警电话。第一次报警录音记录显示,刘鑫向门外喊“把门锁了,你(注:指陈世峰)不要闹了”,随后录音中出现了女性(注:指江歌)的惨叫声,刘鑫向警方称“姐姐(注:指江歌)倒下了快点”。第二次报警录音记录显示,刘鑫向警方称“姐姐危险”。
杀人事件后
江秋莲与刘鑫因江歌死亡原因等产生争议,刘鑫在节日期间有意向江秋莲发送“阖家团圆”“新年快乐”等信息、并通过网络方式发表刺激性言语,双方关系恶化。
从上述行为可知,本次事件前,陈世峰纠缠、发微信等行为显示其主观意图是纠缠刘鑫,刘鑫搬离陈世峰住所、谎称有男友等行为显示其主观意图是躲避陈世峰的纠缠,双方的主观意图均不涉及杀死或伤害第三人江歌,江歌仅在两人中起到缓冲作用。
以下着重分析双方在2016年11月2日至发生侵权事件的11月3日凌晨各方的行为:
陈世峰携刀、埋伏等待等行为显示其主观意图是伤害刘鑫,刘鑫逃避、锁门等行为显示其主观意图是躲避陈世峰之伤害,并意图让江歌帮助其处理;
陈世峰在不能接触到刘鑫后,激动下主动实施了伤害江歌的行为,其主观状态为故意;刘鑫独自进屋锁门将江歌留于楼道之中,其主观意图是躲避陈世峰伤害,让江歌代为处理,刘鑫多次收到陈世峰的恐吓短信、陈世峰的纠缠等显示刘鑫明知陈世峰的危险性,但没有告知江歌陈世峰的危险升级,更轻信江歌能免于陈世峰的伤害,刘鑫就此存在明显过失。
陈世峰系故意,刘鑫系过失,两者不存在共同故意、共同过失,江秋莲依据“意思联络说”主张共同侵权,两者的意思联络难以证明。另,陈世峰之单独行为可造成江歌死亡,刘鑫之单独行为不足以造成江歌死亡,故两者不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1171条5承担连带责任。
由以上分析似乎可以解释城阳法院没有按照江秋莲及其代理律师的观点,认定刘鑫与陈世峰之间的基于共同意思联络而导致共同侵权的内在原因。
三、问题的深入及拓展
显然,虽行为方式不同,但陈世峰、刘鑫在江歌死亡的问题上均存在过错(含故意和过失),且与江歌之损害后果均存在因果联系,根据《民法典》第1172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陈世峰、刘鑫应对江歌之损害后果承担按份责任,江秋莲可分别向陈世峰、刘鑫主张损失。
关于陈世峰、刘鑫各自就其侵权行为应承担的份额,因刘鑫与陈世峰长期存在感情纠纷,11月2日双方纠纷升级,刘鑫对全过程是参与且明知的,11月3日凌晨当陈世峰携刀冲至二楼,与走在后面的江歌遭遇并发生争执,走在前面的刘鑫打开房门,先行入室并将门锁闭,刘鑫已经知道陈世峰与江歌之间的争执,但是刘鑫轻信能够避免不利后果的发生,最终导致了江歌的死亡;换言之,虽然直接致害人并非刘鑫,但如果没有刘鑫的锁门行为,江歌的死亡可能不会发生,笔者认为刘鑫应承担次要责任。
难以回避的一个问题是,根据日本的相关判决书,陈世峰被追究刑事责任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责任27,578,806日元(人民币1,532,278.46元),而刘鑫在日本没有被追责(包括刑事责任及民事责任),且相关判决均没有在国内承认与执行;江秋莲启动的国内民事诉讼仅针对刘鑫,不包括陈世峰。此时,如何在国内和日本两个不同法域的不同判决之间实现两位侵权人之间的主次责任,这是在现有法律框架下难以解决的问题。笔者理解,这可能也是城阳法院以单独创设的“救助关系、安全保障义务及注意义务”要求刘鑫单独承担侵权责任的重要考虑因素。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因刘鑫在本次事件中不是职务、业务上负有特定责任的人员,而陈世峰与刘鑫存在严重纠纷,刘鑫为使本人的人身权利等免受陈世峰正在实施的危险行为(陈世峰携刀冲至二楼),采取了锁门等避险行为,属于紧急避险6的范畴,但确有紧急避险过度之嫌。本次事件中陈世峰携刀伤害的目标是刘鑫,假设刘鑫直面陈世峰,刘鑫之生命权、身体权要受到侵害,刘鑫保护的是自己的人身权利,客观上损害的是江歌的生命权,但刘鑫的紧急避险采取措施实属不当(进门后锁门将江歌留于门外),并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害(江歌死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82条7、《民法典》第182条8,刘鑫应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换言之,因损害的利益已经大于被保护的利益,刘鑫应当就其行为承担责任,进而实现目前一审判决的结果。
四、如何看待和理解法院的一审民事判决?
笔者赞同(2019)鲁0214民初9592号民事判决的判决结果,认为其符合法律人及一般社会公众对于本案实质公平的理解,但法律依据及具体论述上有待商榷。
第一、民事赔偿责任。上述民事判决建立在公民的生命健康权不可侵犯(侵权范畴)的基础上,但城阳法院提及的“救助”见于《侵权责任法》第53条9,“安全保障义务”见于《侵权责任法》第37条10、《民法典》第1198条11,涉及机动车事故中的救助,以及机场、体育场馆等公共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本案中,江歌与刘鑫均为个人,并非上述两部法律规定的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故城阳法院的上述法律分析并无明确的法律依据。但无论从分别侵权行为下论述侵权人刘鑫的按份责任,还是在紧急避险过度下论述紧急避险人刘鑫的适当民事责任,两条法律分析路径均有明确法律依据(虽前者涉及到两个法域下两个判决的冲突及协调),且两条路径均指向了刘鑫应承担次要或适当责任,该结果与该民事判决刘鑫承担江秋莲合理合法损失(除精神损害抚慰金外)的39.9%基本吻合。
第二、精神损害抚慰金。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12,江秋莲因江歌之死亡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没有争议,且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有
其合理依据。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人死亡情形下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数额通常为10万元,民事判决显示刘鑫有两个侵权行为,分别是其与陈世峰共同造成了江歌死亡的侵权行为和刘鑫在事发后发表刺激性言论,加上社会影响等,法院根据行为情节、损害程度、社会影响酌情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20万元,属在法律之内,情理之中。
五、结语
法学是一门科学,任何法律结论需要经过严谨周密的法律推理与论证,尼尔.麦考密克认为“法律制度的规则为正义提供了具体的含义,在通常情况下—即演绎性证明方式可以游刃有余地展现自己能力的场合,通过适用相关的和具有可适用性的规则,这些正义观念的要求是能够很好地得到满足的”13,故法律人应在法律范畴内适用规则寻求正义,避免“道德办案”。
1. 如孙宪忠教授提出“对本案的分析,我认为还是要仔细阐明过错和因果关系。道德底线等方面的论述不可以多讲,否则还是法理不明,给人一种法院以道德办案的印象”。
2. 因本案的事实众说纷纭,本文仅以一审民事判决书、律师代理词中所涉事实作为分析的基础。
3. 经笔者核查上述民事判决引用的法律依据,法院未引用救助、安全保障的相关法条,笔者又以“救助”、“安全保障义务”为关键词检索的法律法规等,法律法规无上述证明的依据。
4. 共同侵权的法律依据为《侵权责任法》第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8条。
5.《民法典》第1171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
6.《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1条: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第一款中关于避免本人危险的规定,不适用于职务上、业务上负有特定责任的人。
7.《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182条: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民事责任。危险由自然原因引起的,紧急避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可以给予适当补偿。紧急避险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紧急避险人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
8.《民法典》第182条: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民事责任。危险由自然原因引起的,紧急避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可以给予适当补偿。紧急避险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紧急避险人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
9.《侵权责任法》第53条:机动车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该机动车参加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机动车不明或者该机动车未参加强制保险,需要支付被侵权人人身伤亡的抢救、丧葬等费用的,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后,其管理机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
10.《侵权责任法》第37条: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11.《民法典》第1198条: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承担补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1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因生命、身体、健康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13. 英 尼尔.麦考密克著 姜峰译 法律出版社 第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