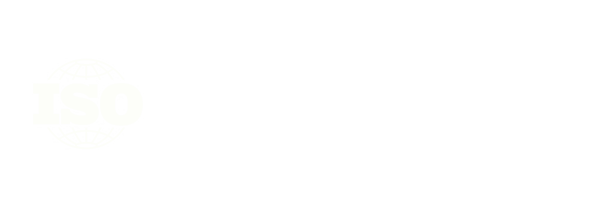八千里路
2019.04.17 李骐
那年我去洛杉矶去拜会一个赫赫有名的律所,是开着在机场租的车去的。我对洛杉矶不熟,GPS反应又慢,一个急转弯,车的前轮碰擦了街沿,轮胎瞬间爆裂。我只能在路边停车,按着保险公司的号码打过去,请他们来拖车换胎。因为不想迟到,我一边等着保险公司的拖车,一边琢磨着是否可以自己换胎。结果,我真的满头大汗地把备胎换上了。再给保险公司电话,他们的车至少还有20分钟才能到。我告诉他们不用来了,自行开车赴约。当穿着西装、背着双肩书包、满手油污的我与穿着夏威夷式的花衬衫、美国最赚钱的诉讼律所的创始合伙人见面时,我并没有觉得十分突兀。
这段小小的插曲已经过去很久,但今天我突然想起,仿佛正是君合的写照。我们都有不同的职业习惯。我的西装反映了自己在上海和纽约生活多年的经历,双肩书包则暴露了我常年旅行、并在旅行中工作的习惯。我们一直与一流的客户和伙伴合作,但这并没有让我们忘记,我们所有的工作其实都从满手油污开始,不问贵贱。我的习惯和特点多来自那些亦师亦友的君合同事们。毕竟,到2019年,我分别在上海、纽约和硅谷和他们一起度过了十八个春秋。
“人在孤身一人的时候,是最不孤独的,因为只有在这时候,他才获得一种大自在”。
——梭罗
上海曾经有一个东华律师事务所,创始人就是马建军。老马创建这个事务所的目的就是做劳动法。可东华所成立的时候(1995年1月1日),新中国第一部劳动法才刚刚生效,而且,当时大多数人(包括我)并没有把这部法律看得很认真。
我认识老马的时候自己才20几岁,是一个初出茅庐、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当时上海律师界的同行们,大多与我的经历截然不同。他们或是工作多年以后才转行做律师,绝大多数都是大学本科以下的学历、或是工农兵大学生,而且,在学校真正学法律专业的也是少数。即使有,也极可能是1949年前读的法律(我在第一个律所的导师蒋鸿礼先生,就是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在东吴大学读的法律)。1991年我开始做律师时,是当时上海律师圈仅有的两个法律专业硕士之一。那时在上海,法学院的学生毕业后都是去法院或检察院工作,律师本身就是个小众,并且大多数做的都是街谈巷议的刑事案件。我有幸看着比我年龄稍长几岁的律师从骑凤凰牌自行车、比亚乔助动车到幸福牌摩托车的过程。我的第一个律所全所只有一辆桑塔纳汽车。
1991年,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我不知不觉中就接触到越来越多的西装革履、小车接送、出入五星级宾馆的生意人、跨国公司职员和专业人士了。他们常常有着比局长更高的待遇。当时上海的局长也就只配备一辆奥迪A6,而我的一个客户则有两辆劳斯莱斯。当然,这是少数。更多的情况是,在上海几乎所有市民都坐公车或骑自行车出行的年代,我的一些客户或同行可以任性地叫出租车。有一个香港律师为了在毛毛细雨中保护他的西装,居然叫了一辆出租车从南京西路北面的利兹卡尔顿(当时是香格里拉)送他到南面的锦沧文华,当中只有100米的距离!我第一次作为工作餐吃海南鸡饭,发现一份饭居然要100多元人民币,而当时作为研究生毕业的我,每个月的工资也就比这个数字多不了多少。不仅如此,我的客户多是外国银行、外资酒店或外国律师、会计师,说起来都是国际名校毕业,有着眼花缭乱的经历。坦白说,这些或扣着金袖扣、或画着淡妆的(当时化妆的女士甚少)的成功人士吸引了我绝大部分的注意力,而他们,是不谈劳动法的。
随后,我遇见了马建军。
那时的老马,精瘦。说话轻声细语,举止彬彬有礼。如绝大多数干部一样,他常年穿一件中山装,发型简单但头发乌黑。马建军的正式官职是上海市律师协会秘书长。因为我常参加律协会议,就和他相识。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们相约一起去听西洋音乐会、喝茶。和老马夫妇一起分享音乐、艺术实在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在我临去美国的时候,老马还送了我一张恩雅的CD。
1994年的一天,老马找了个机会和我坐下,认真地告诉我,他要辞职了,要成立一个律师事务所,只做劳动法。90年代初,从机关辞职去创立事务所、放弃所有公务员的福利,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我自然是非常钦佩。但在所有人都在做非讼律师、商业律师时,有人跟我说他只做劳动法,令我满腹狐疑。
他的东华所后来真的成立了。兴奋过后,他的苦恼也随之而来。从市场上听到的关于老马遇到种种困难的风言风语,让我不禁为他担心。
98年,我搬去了纽约,五年后回到上海时,我才再次见到老马本人。仅仅五年,他已经头发花白,但却是中国劳动法毋庸置疑的权威。他告诉我,后来他无心在自己创办的律所恋战,离开了东华,加入了君合。在这里,他如同老鼠掉进了米缸,他看到了劳动法的无限可能。这里有更多、更大的客户和更复杂的问题。几乎所有大项目都有劳动法的问题。无论是合资收购、员工罢工、工会危机,君合的大客户和大合伙人偏偏就不懂劳动法,个个期待着老马的帮助。老马在君合每天激动地活在他八年之前的预言之中--劳动法问题层出不穷,但能够处理劳动法的律师却寥寥无几。
我们这代人,大多数是凑巧赶上了时代,而老马则是在没有成为律师时已经看到了即将来到的巨浪。他是一个真正的前卫。
在上海和老马一起工作的时候,我渐渐开始更加留意老马以前的经历。他做过装卸工、开过大货车、与死亡擦肩而过(参见《君合人文》老马的文章《那年我18岁》,http://www.junhe.com/humanities/195);也做过上海司法局局长的秘书,在劳改机构里和看守和囚犯称兄道弟;在律协任职时,他与世界各地顶尖律师接触甚至有很深的交往。他随后的律师执业得益于他那些年真实观察到的人性的狡诈、残酷和良善,是一个十分接地气的律师,而这些素养和能力,恰是许多从法学院毕业后直接做律师的精英们所不具有的。
老马有很多粉丝,是源于他的背包旅行和游记。他的旅行不是去舒适之地,而是去受苦、去拥抱自然的狂野和平静、去经历他人的挣扎和欢乐(参见《君合人文》老马的文章《旅行的意义》,http://www.junhe.com/humanities/184)。他攀登乞力马扎罗山,他在北极光下夜宿;他在阿富汗差点被泥石流淹没,在澳大利亚为躲避大货车将摩托车从高速公路驶下山坡,然后提着一条断臂再回到公路、开摩托车去几小时以外的医院就诊。他住最便宜的小酒店、吃手抓饭、和各种陌生人一起喝酒畅饮。这些旅行,造就了老马的阳刚、豁达、智慧、狡邪、真实、细致、无畏、直言不讳、讲原则又重情谊、悲天悯人集于一身的品行。
我们这个年代目睹很多成功的故事。我年轻时不了解,成功常常是一个诅咒。我见过二十多岁就油腻的成功人士,成功之后完全失去了生活的目标、激情或乐趣。老马知道这其中的危险,于是在荒山野岭之间、在饥渴虔诚的人当中脱胎换骨。因此他更敏锐,常常看到我们所熟视无睹的事情。老马借着他的旅行拒绝被现代都市的舒适、狭隘、庸俗、堕落所孤立。
我早年不理解老马为什么能够预言到劳动法辉煌的日子,因为那时候我的世界实在肤浅。
朱坚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岳飞
一,
朱坚1986年从复旦生物系毕业。早听说他在大学本科时候就在深圳创业,后来和他幼儿园时代就认识的女友成亲,一起来到美国。这是真的,因为这个女友至今还是他的妻子。
二,
据说美国的大学有一条鄙视链,说的是耶鲁鄙视哈佛、藤校鄙视准藤校之类的,但加州理工则鄙视包括所有藤校在内的一切其他学校。当然这不是事实,但也说明了加州理工的独特地位。
1991年,朱坚从加州理工毕业了,拿到了生命中的第一个博士,还拿到了世界著名药厂默克公司(Merck & Co.)的工作,定居在风景如画的宾夕法尼亚,同年还生了个女儿。
那年,他才25岁。人生赢家啊!迄今为止,朱坚没有错过人生任何一站—江南第一学府、美国最有竞争力的大学、娶青梅竹马为妻、顺便还有创业经历,如今摇身一变又成了一个科学家,还有一个千金,你还指望什么呢。养条小狗,享受生活吧!
三,
成功来得太快,人就犯贱,朱坚也未能免俗。这一天,也就是朱坚做了科学家后五年的样子,他又腻烦了朝九晚五的工作,策划再次创业了。他考虑读法律、或者读商科,但到底读哪一科更好呢?朱坚不知道,干脆都读吧。钱从哪里来呢?借吧。他真的就放弃默克的金饭碗、同时申请工商管理硕士和法律博士,随后被哥大商学院和法学院同时录取,1995年在纽约开始了他新的冒险。
我就是在朱坚在法学院读书的最后一年认识他的。那时,他除了有一位美丽贤惠的太太、一个漂亮活泼的女儿之外,只有一架旧的尼康相机和二十五万美元的学生债了。他有半年,需要每个月向信用卡公司借钱才能还上他旧信用卡上的负债。
那时,他已经三十二岁了。
四,
人生从来是不公平的。我毕业的时候,只拿到两个公司的面试、最后终于有了一份工作;而朱坚则一口气拿了十几份工作邀请,有律所、投行,也有咨询公司。最后,他把所有的工作邀请都拒了!原来,他的创业公司拿到了融资。为了这次创业,在我们其余的法学院毕业生都在准备律师资格考试的两个月里,他每天都在加班工作。直到考试前十天,他向同事们告假,说他必须复习迎考了。
你猜对了,他居然一次通过了加州律师资格考试。这个全美最难的律考,他只用了十天的时间准备,没有参加任何补习班。
那是1999年。
五,
转眼到了2001年秋天。我自己在美国的苦行开始有了转机。两年里,我在华尔街律所工作,通过了纽约州的律考;几次辗转,哥大再次录取了我,这次是法律博士;应君合朋友们的邀请,我加入了这个我仰慕已久的律所。三十五岁,我的生活重头开始。
一天傍晚,我的电话响了。是朱坚!如往常一样,他说了几句话就单刀直入。他的初创公司在两年里烧掉了几千万美元后破产了,他此时正在加州律所找一年级律师的工作。我当时听了之后暗暗庆幸自己没有拒绝君合合伙人的邀请,不然毕业后我也得和他一样去找受薪律师的工作。让我欣慰的是,朱坚给我电话的时候并不抑郁,甚至有些兴奋。我们在电话里说到,人生所经历的一切试炼,都是为了准备一个更好的将来。
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是真心相信。
我所不知道的是,他当时还欠着那二十五万美元的学生债。家里除了需要抚养一个十几岁的女儿之外,还要喂养一个刚刚一岁的儿子。
朱坚实在是不甘心。在公司最后的日子里,他回到美国,一个人驾车来到大峡谷背包旅行,随着旷野的日出日落作息。我想象着他当时的心情时而畅快淋漓、时而心如止水、时而恍恍惚惚……正在他恍惚之间,他从山上滑了下去,一根树枝刺穿了他的膝盖,顿时,血流如注,他的膝盖立刻肿了起来。
朱坚挣扎地从山下走回大路。他不敢去看病,因为他没有医疗保险。不顾周围人异样的眼光,他瘸着腿去超市买了一块大冰块,压在膝盖上,然后驱车十几小时回到家中。
朱坚病倒了,在床上躺了整整一个月。
六,
离开法学院后再找一年级律师的工作并不容易。律所都喜欢规规矩矩的学生,最好是一张白纸。朱坚面试的时候,面试他的律师揶揄他说,你听起来更像是一个CEO,而不是受薪律师。没错,他的确是CEO啊。
由奢入俭难!
但是,还是有一个伯乐相中了朱坚,给了他律所的工作。朱坚一生中从来没有如此这般地珍惜他曾经十分不屑的为人打工的机会。他一年工作加上旅行有3000个小时。四年以后,朱坚就成为了加州一个非常知名的知识产权律所的合伙人。再不久,他又成为了另一家全美知名律所的中国办公室的管理合伙人,帮他们设立了北京和上海办公室。
七,
那几年,我在上海,朱坚在圣塔莫尼卡。他在南加州和上海之间常来常往,因此我们就有机会见面。我们分别有两个孩子,吃自己劳作而得的粮食、喝自己辛劳而获的美酒。我们两个那几年都顺风顺水,生活对我们真是非常厚待。
但我隐约觉得,朱坚还有下一个轮回。
果不其然,有一天,朱坚又来电话了。这次,他想加入君合!经过几年在中国法律市场的探索,他发现中国律所才是发展中国法律业务的更好平台。为此,他和他的伙伴准备两年内向君合借最基本的生活津贴,打造一个君合知识产权团队。
我们张开双臂接纳了朱坚和他的伙伴们。2010年,君合有了硅谷办公室和专利团队。
这两年,我和朱坚有了真正的一手接触。他可以早上六点开始工作到第二天早上一两点,当中全是背靠背的会议,中间只吃一顿饭;他每年中美之间会飞行至少有五六七次,然后还有往返欧洲、和在美国国内、中国国内穿梭,一年加起来也有十几次的飞行。他可以直着身体坐经济舱十几个小时、住经济型酒店,也可以打一整天高尔夫、去最人迹罕至的酒庄喝最名贵的红酒、吃最肥厚的牛排。他是一个永动机,有永远用不完的精力;他又是一个钢铁侠,失败了可以重新再来。因为他的表率,仅仅八年时间,君合专利组从三个合伙人开始,到今天已经是一支在上海、北京和硅谷的五六十人的律师队伍。
朱坚曾只是一个杭州少年,辗转上海、深圳、南加、宾州、纽约、北京、硅谷,现在是君合专利团队的管理者、一个律师、投资人、科学家、品酒师,喜欢高尔夫、热爱运动,珍视朋友和社区、不惜为集体和理念付出,一个独立和自我奋斗的崇尚者、一个单纯的丈夫、慈爱的父亲,一个脚踏实地的梦想家。
他的工作的热情、速度和强度,经常会让周围的人感到窒息。自我认识他已经二十年了,他从来不知停歇,也真心不了解别人为什么需要停歇。
幸亏世上只有一个朱坚。
“ 你们没有开垦土地,也没有建造城邑,但我赐给你们土地和城邑,使你们住在其中,享用别人栽种的葡萄园和橄榄园的果子。”
——《约书亚记》24章13节(中文当代译本)
初见老周
98年我去美国读书的时候,多少是为了遂我一个固执的心愿,就是在名牌法学院上学、在华尔街工作,证明我很有才干。成为这精英一族的标志就是穿名贵的西服、在昂贵的俱乐部吃饭、孩子上英国的本科、美国的研究生院。为了这个心愿,我背井离乡,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后来,我真的在哥大读法律、并且在华尔街的律所工作了。只是有一样,每天在华尔街附近上班的时候,我发现周围那川流不息、无论男女都穿着清一色蓝灰色高档西装的人流,大多数脸色苍白、没有笑容。
老周和他们不同。
老周是君合纽约办公室的创始合伙人。法律和历史教科书上的湖广债券案是老周在外交部领衔处理的案件。老周也是中美恢复邦交后中国第一位送哈佛法学院攻读硕士和博士的学生,马英九的同学。这种种光环都让我想象老周是一个阅历丰富、洞察一切、令人敬畏、并且身材魁梧的律师。当2001年我终于见到老周时,他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老周头发乌黑、面色红润、举止从容,没有华尔街永远流行的紧张神情,比同龄人看起来年轻许多。他穿了一件没有任何牌子的旧呢子外套,里面的衬衣袖口和领子明显磨损很久、却干干净净。他手里提着一个本来是黑色,但因为年代久远,周边已经发白的公文包。这一切,都让我大跌眼镜。
2001年的君合座落在纽约世界贸易中心一座77楼,是两个10平米左右的房间,加一个小小的客厅,因为只有老周和我两个人,显得有点冷清。世贸中心整个大楼不能开窗户,因此如果有人在办公室抽烟,烟味就很难散去。老周上班第一天就问我是否抽烟,我很不好意思地告诉他我抽,他就对我说,他不抽烟,但他一点不介意别人在屋里抽烟。我当然知道不抽烟的人其实对烟味是及其敏感的,因此老周的这番话让我觉得他怎么能那么纵容我呢。
几年后,我戒了烟。
孤独的纽约
和老周在一起,我慢慢知道了纽约办公室的创业史。这个中国律师历史上第一次在海外设立的办公室,当时在国人眼中尽是光鲜,但其中的艰辛,非自己经历是不能体会的。
纽约办公室在我之前就是老周一个人。那时,中美之间没有什么法律业务,有的话也被几个纽约、芝加哥的大所垄断,因此,君合办公室开始只有一些文件翻译的工作。老周翻译、周太(以前在国内是一个军医)打字。老周家住新州,坐地铁加州际通勤车(PATH)到世贸中心办公室至少要一个多小时。纽约的冬天异常寒冷、相当于中国东北的冬天,气温可以达到摄氏零下十几度。曼哈顿的下城,冬天的风大到可以把人吹走。
在这种冬天,你会愿意在没有其他同事作伴的情况下,离开温暖的家、要先开车去车站坐火车或州际通勤车、再换乘地铁、高峰有快车的情况下也要一个多小时去另外一个州的、空荡的小办公室里办公吗?
这样坚持几年、十几年?
曼哈顿律所林立,90年代初大所一年级的律师起薪就是八万多美元,老周那边律师费第一年才挣一万多,是什么让老周坚持维持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君合分所?
多少年来,中国人在纽约开的律所,几乎无一例外是唐人街的移民所。或有决心做大的律所,不多久,也分分合合、各奔东西。老周也亲眼见到许许多多中资背景的公司和律所开张时场面豪华,但不久就关门走人。
但君合纽约25年来从来没有关过门,哪怕是在911那天,我们在世界贸易中心的办公室被毁的时候(参见《君合人文》我的拙著《9月11日》,http://www.junhe.com/humanities/176),很快就在另一个大楼开始办公了。(参见《东方律师网》转载君合的通告http://www.lawyers.org.cn/info/b9b539f083054842a8a74cdca54c2663)
因为老周的坚守,君合终于在纽约逐渐壮大。今天,君合的纽约所已经有四个合伙人、四五个律师、50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座落在曼哈顿中城洛克菲勒中心。纽约最大的圣诞树、溜冰场、圣帕特里克大教堂、SAKS FIFTH AVENUE和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都近在咫尺。办公室所有的窗口看出去都是地标建筑。当年加入君合纽约的律师,今天已经是这个办公室的管理合伙人了。
可是老周,那么多年,你可曾感到过孤独?
最优秀的人(the finest person)
君合有个客户,是座落在纽约、全世界家喻户晓的化妆品巨头,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声望和稳定的收入。老周是开发和负责这个客户的合伙人。十几年来,这个客户几乎在中国的每一个商场落地,但是,直到今天,就算绝大多数的法律事务都发生在中国大陆,他们还是坚持每年和老周一起在纽约开会,商讨他们在中国的法律和合规策略。
君合还有一个客户,是一个富有的国际经济组织,对业务要求非常之高。和君合一起负责其中国法律事务的是魔圈所(Magic Circle)的资深合伙人,一位伯克利毕业、90年代初就在中国工作的美国律师。每次这个客户有事,他必然指定和老周一起做,因为这位中国通只相信老周一个。
我和老周一起去见过不少在美国的律所和客户,所到之处,你都可以感觉到他们对老周由衷的尊敬和信任。
我们的同事也同样尊敬和信任老周。其中一个合伙人曾说,老周是她见过的最优秀的人(the finest person)。
老周有什么神奇的魅力、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
有一个才高八斗、却四处怀才不遇的北大法学院毕业生,在世界各地游学多年,落脚美国。有一天他终于想起,在遥远的中国有他可以称为家的地方。于是,他决定终止他的流浪生涯回国。
只是有件事情比较麻烦,他没有时间卖他的旧车了。
多年流浪的他,口袋里也是叮当作响。
老周对他说,你看看你的车市场上多少价,我加给你1000美元,你卖给我。
这个朋友后来成为了一家国际大律所的合伙人。
纽约是一个驿站,多少人来了又走。君合的许多同事都有在纽约有求学和工作的经历,之后又天各一方。
老周留下了。
他不光留下了,他也成了我们最温暖的驿站。老周每年都会在家里举行节日聚会,招待君合的同事和老友,人数一年胜似一年。我在纽约工作的时候每年都参加他家里的聚会,后来到了上海,每次回纽约,多半会住在老周家里。他家的信箱成为我们这些人在美国的通讯地址;君合许多同事在美国求学、定居,甚至他们的下一代在美国留学、工作,都会以老周家为圆心,方圆几十里地,环绕而居。他家里永远有一张床是为我们准备的。
他也把这样的聚会和客房留给他外交部的同事、教会同工、远房亲戚、朋友同学。他资助他们上学、帮助他们寻找工作,也会忍受着肩周炎、来回一百英里,去接送他并不熟悉的另一个办公室的新同事。他是许多中国人探索新大陆的第一站、他也常常是美国人了解中国的第一站。
但是,他也会告诉你,他只是一个热爱种菜钓鱼、养鹅逗狗的安徽农民。当他全心帮助你的时候,你不会感觉有任何压力。
到今天,我还是常常想念多年以前、当老周和我还要共用一个办公室的时光。那时,一踏进办公室、一种祥和扑面而来,和常人印象中的纽约完全不同。君合纽约对我来讲、是一个即使在寒冬也无比温暖,洋溢着老周特别的平和、慈爱、坚定、智慧、慷慨和谦卑的地方。这个温暖,无疑感染了纽约所有的同事、以及接触过他的所有人。
***
在君合的日子,我有许多时刻可以铭记:
当我参与全球最大规模的公开发行上市(IPO)、或最知名的并购项目的时候;
当我四十岁时,还连续通宵四、五个昼夜,按时完成所有文件的时候;
当当事人走遍许多律所未果,而他的商业计划却在我的帮助下付诸实施的时候;
当在交割前发现一个重大法律问题,交易、客户命运、职业操守和君合信誉命悬一线,而对方或是权倾一时的领导、或是我多年敬重的老友,我却必须看着他的眼睛、艰难地说出那个“不”字的时候……
我感恩在君合参与过非常挑战的案子、有机会和世界各地最优秀的同事或对手一起工作。回头望去,那些挑灯夜战的苦旅、风光无限的颁奖晚会、令人咋舌的交易金额,在我脑海里都很快褪了颜色,留下最多的是许多名字和熟悉的脸庞,那些曾是我梦寐以求可以一睹真容的英雄,或只是默默无闻、却多年来始终工作出色、还跳得极棒街舞的普通员工。他们每天都近在咫尺。他们与我分享他们的耀眼成就,也分享油盐酱醋,以及风光背后的、有血有肉的心路历程。他们的出色和谦卑都让我无以自夸。
君合最优秀的不是最佳交易、精英律师。这些都早不足以吸引我。君合最优秀的,是那些各式各样有故事、有趣味的人。
遇见君合是我人生的重新开始。在君合的日子里,轻狂遇见了醇厚、简单遇见了多样、理智遇见了情感、聪明遇见了包容、慷慨遇见了智慧、江河遇见了海洋;
在君合的日子里,我这个上海人同时遇见了南方和北方、东方和西方;
我遇见了我们。